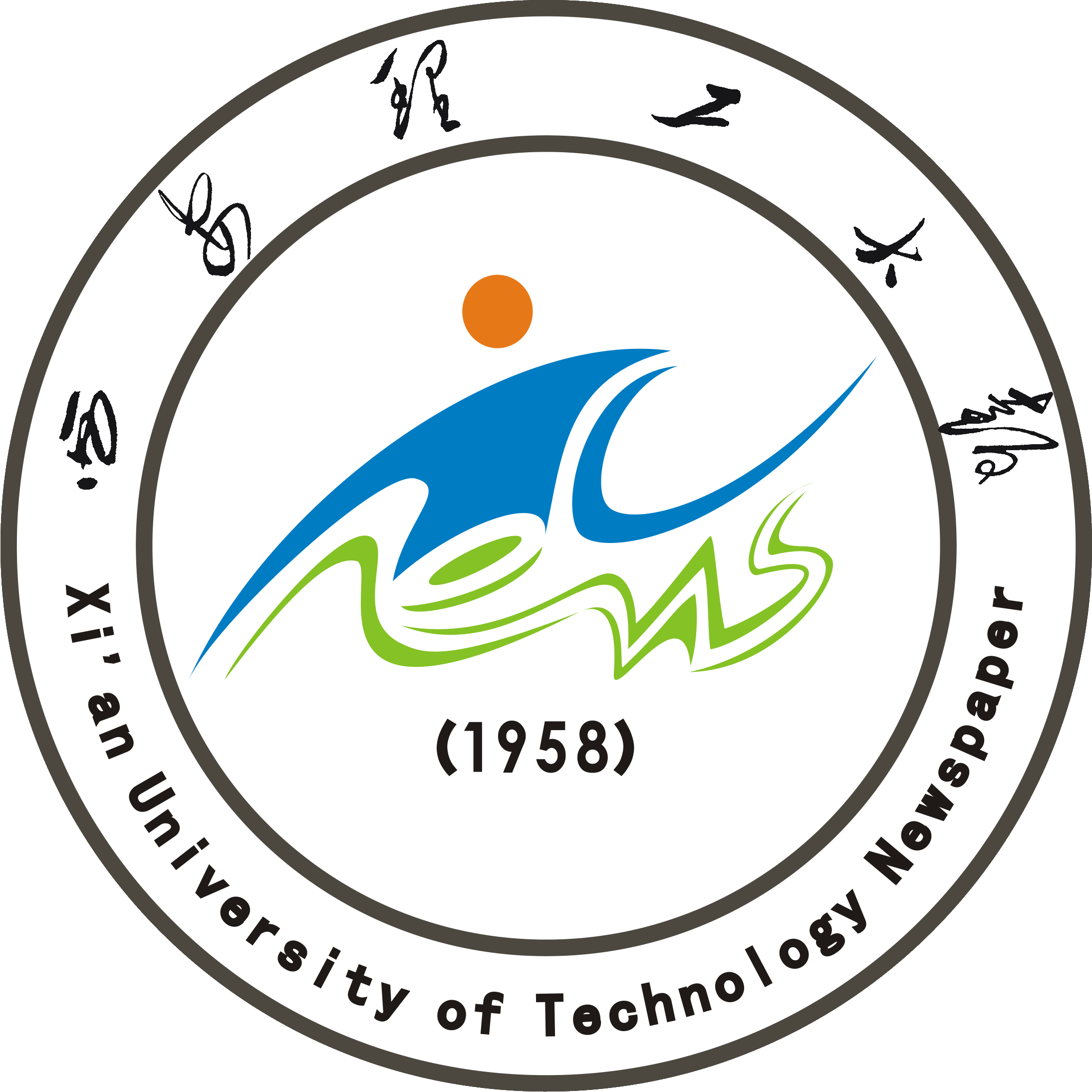父亲已经很久没有在我们面前提起祖母了,我躺在狭窄的车子后座上想到。昨晚为了赶上回家的高铁只睡了两个小时,现在的我脑袋昏沉沉的,费劲地呼吸着车厢内难闻的空气。大半年过去了,我晕车的毛病反倒愈加严重起来了。
父亲坐在前面小心翼翼地开着车,依旧穿着那件蓝黑色的旧棉袄,那是我初三那一年买的,父亲在那之后的每一个冬天都穿着它,就像是把时光披在了身上一样。淮安的冬天不同于西安,西安的冬天就像是隔靴搔痒,浅尝辄止,而淮安的冬天却如同敲骨吸髓一般,将寒冷混着湿气注入身体里的每一个血管与骨节,一直到语言都变得短促而冷清。天空阴沉沉的,街面上几乎见不到行人,清冷的天光透过车窗照在父亲的身上,他比夏天的时候更加的精干与壮硕。
等我们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入夜了,父亲领我去了我的房间。家里的布置和去年夏天截然不同,补习班所有的桌子与凳子都没了,已经被父亲收拾回了胡桥老屋子里了。购置了一台崭新的电视,润园的电视柜与沙发也被搬了回来,本来空旷的客厅被布置得满满当当。我的房间在三楼的旧教室里,大红的床单与被子,墙面上贴着吉祥喜庆的红字画。这是父亲与母亲为姐姐布置的婚房。
母亲给我端来了她做的包子与南瓜饼,香甜软糯,满满当当的两大盘子,放在床边的柜子上。母亲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坐在我的床边,上下打量着我,笑眯眯地说:“也没瘦嘛,我还以为你瘦了呢。”
“最后一个月不是隔离在宿舍嘛,也不能出去锻炼运动。”我不好意思的回复着:“这不是我姐的婚房嘛,我睡这边做什么啊。”
“睡呗,这有什么的呀。”母亲满不在意地说道,随后又担忧地望着我:“你看看你没瘦,也不知道你尿酸降没降下来。”
“我在西安的饮食都是注意的,不敢吃这个也不敢吃那个,那降不下来,我能怎么办嘛。”
“那你也要锻炼啊,光不吃也不行唉。而且你望望你尿酸多高啊,你爸才五百多,你都六百多了。”
“知道勒知道勒,那我当时不是隔离嘛,买饭什么的也不方便,人个买什么你也就只能吃什么,没得办法啊。”
母亲和我又聊了几句之后就起身下楼去了,她要去商联边上的美容院去做保养。父亲依旧站在房间的窗口旁边,靠着二姑父刚打的书柜,翻找着手机去找社区负责人报备。我疲累地躺在床上,从床边拿了一瓶酸奶,一边喝一边从旁边的盘子里拿起包子吃了起来。直到困意像死亡一样向我袭来。
母亲做的包子里面放满了南瓜和肉汁,一口下去糯糯的,伴着荤油的味道从喉咙里滚下去,从胃子里一直暖到全身。由于三楼的房间实在是太大了,空调也是三四年前的老物件,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再加上三楼顶上没有隔热层,所以我仿佛永远都是呆在雪地里一样。在这个冬天之后的许多时间里,我都是靠着这一口在我姐姐的婚房里过活。
父亲每一天的早晨与下午都会去街面上找人打牌,母亲则是在午后去搓会麻将,而上午就在家里忙前忙后地收拾忙活着。我总是呆在三楼的房间里,在那里看书与写字。直到母亲在楼下大声呼唤我去吃午饭。
我很久没有回岔河镇了,我对外面的街面与人群感到亲切又陌生,他们在我的窗户下面熙来攘往,而我却在我的窗台独自观看。我喜欢观察窗外的一切,看街对面的天台,天台上的自行车与太阳能。有时候晚霞会从栅栏那里投进我书桌背后的那一大块空地上,我就会坐在那里,感觉自己已经飞在了天空上。
年前的生活日复一日地这样过去,循规蹈矩,整座城市都仿佛睡着了,和我离开时的生活一模一样。直到有一天傍晚,母亲从麻将桌上回来,唤我下来吃饭。母亲在桌边一边剥着花生米,一边在那看着电视,看见我下来了就对着我说到:“哎呀,你一定要注意锻炼啊,你看看你胖的呢。”我不耐烦地应着:“嗯呢嗯呢,知道勒。”母亲每天都喜欢这么唠叨我。听出了我的不耐烦,母亲毫不在意似的继续说着:
“你看看现在你爸都注意锻炼了,锻炼身体嗷,你望望你现在这个尿酸啊多高啊。”
“我晓得哎,我这不是每天晚上都出去跑一转子嘛。”
“你才跑多长时间啊,三十分钟都没得吧。我跟你爸每次都跑一个多小时呢。锻炼身体嗷,身体才是最重要的。”母亲不满地说道:“你看看那个邵军啊,才多大啊,就都不能了。”
“邵军?”我惊讶地重复道:“邵思源他爸?”
“是的啊,得了癌症了,当时你爸学校的老师都捐钱呢,当时我和你爸害怕呢,都不敢瞎吃东西了。你望邵思源他爸呢,在食堂吃饭呢两大碗饭,就往肚子里撑,能吃那么多吗?啊?”
“他不是转到湖小去了?”
“是的啊,但是你爸他们也捐钱了。你说他们家家庭条件也不好,邵思源他妈也不做工,好看是好看呢,就是不找个固定工作,天天打零工,邵思源还上学呢,唉…”母亲继续在那里说着。我突然觉得有点胸闷气短,就推开了客厅的铁门,站在门外的小走廊上。街面已经全黑了,只有路灯在亮着。夜里清冷的空气就像海洋一样,涌入我的胸肺里。我看看天空,却怎么也找不见月亮。
原来我也已经二十岁了,已经快到了该一个人收拾背囊与挥砍前路荆棘的年纪了。
大年三十那天清早,父亲就驱车带我们仨往苏州去。姐姐早好多天就劝我们去苏州过年,我和她也因为各种原因也有两年没有见面,我很想她,也同意这个决定。父亲本来是不愿意的,但是最后也是拗不过母亲和姐姐,最终还是同意了到苏州去过年。
等到了我姐姐家的时候已经是三四点了,姐夫和大伯大妈已经在家里等候了,他们接我们仨上了楼,我们带的蔬菜大包小包的也都给提溜上去了。
父亲坐在姐姐家里的小沙发上,母亲到厨房里给大妈打起了下手。大伯坐在桌子旁边,和父亲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姐夫去开车接姐姐下班来。我局促地坐在毯子上,地暖温温地捂着我的身子。我觉得这一切熟悉又陌生。
年夜饭是我吃过的最丰盛的一顿。无奈的是,以前能敞开了肚皮吃的时候,这年夜饭都是随便做的几样菜肴;现在对着满桌的丰盛美食,我却不能够像小时候那样放开了吃了。
大伯喜欢喝酒,一个劲找借口敬酒。他喝多了酒就从一个沉默含蓄的老实人变成了一个侃侃而谈的男人,涨红着两颊在饭桌上嘟嘟囔囔地开始不停地教育着我这样的后辈要加倍努力,表达对姐姐考上博士、努力奋斗的满意与诉说着他自己的人生感悟。父亲坐在他的身边,侧耳听着他的发言,在里面捡取着对他有利的语句对着我继续加强教育:
“文章写得好的人多呢,你望望那个大伯的那个同学,啊,人个也是万集学校老师呢,人个文章写的好呢。不是和你大伯他们一块玩,去图书馆,他说能找到他写的书,还以为吹牛呢,一搜,还真找到了。”父亲在那说着。父亲和母亲不喜欢我的这些梦,认为这些梦不切实际,觉得我们家没什么关系,找不到人指导,是不可能成功的。他们活在他们的人情社会里,而我却始终想着办法洗刷掉我身上那些已经刻入皮肤深处的人情世故。
姐姐的肚腹已经有着不小的隆起了,有一条小小的生命在里面翻来滚去。“戚柒预产期是六月份。”姐姐对我说道。
“六月份,我回不来啊,今年暑假我都不一定能回的来,要下工地。”我遗憾地说。
“你舅舅都不来看你小侄子呀。”姐姐抱怨着,一边抚摸着肚腹。姐姐发呆时的眼神和我一样,呆滞又涣散,将整个世界与我们隔离开来。
我在旁边讪笑着,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望着姐姐挺起的肚子,我突然想到,肚子里的那位是我们家的最新一代的成员,可是他的记忆里不会有我的祖母和那些我小时候所遇见的长辈们。他生活在另一个时代里,他有着更加美好纯洁的心灵与躯壳,他将沐浴在我们家庭的下一段的时间里。
等我们再回淮安的时候,父亲母亲已经快开学上班了。母亲在前年就退休了,返聘了一年后,父亲在岔小给她找了一个宿管的工作。每个星期的周一到周四,母亲都得住在学校寄宿治看管那些孩子,父亲则一个人睡在二楼的主卧里。我下楼上厕所的时候,总能看见他拿着手机一个人窝在被窝里刷着视频。我按下冲水的按钮,在水流急促的声音里,我透过卧室门留下的缝隙看见父亲孤独的身躯,蜷缩在大床的一边。
透过厚厚的门板,我突然感觉到我与父亲之间隔着从此以往的三十个热闹或是孤单的冬天,而我正义无反顾地在他们中间穿梭着。
募的耳畔来了一句旧词: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父亲已经很久没有在我们面前提起祖母了,他已经走的很远很远了。他没有再提起祖母,可是他也在慢慢地向祖母走去。
生活依旧循规蹈矩,我在淮安过冬的时候比在西安更喜欢睡觉与发呆。我的精神与躯干都已经被这个地方的空气与湖泊浸染透彻,如鱼得水,如鸟在林。在睡觉与发呆的时候,我总会想起过年时的那些事。这是许多年来最热闹的一次新年,也是最短促的一次新年。我们在姐姐家呆了短短两天半,但是却是两年来的第一次相见。久别却是短聚。上一次姐姐孤傲地带着我在她家里舒舒服服地过了段时日,这一次家里却又多了许多新的人,大家伙一块在苏州城里晃悠着过了一个短年。
在我还小的时候,每一年的过年是最热闹的。祖母那时候还在,我想那段日子也是她最开心的时候。一大早起来贴对子,清扫院子,父亲骑着电动车往村西头的坟茔滩烧纸,我和姐姐起来看电视。那个时候家里用的是一台很大很大的熊猫彩电,后来父母将它卖给了一个远方的亲戚。那个时候胡桥村夜里还算热闹,就是黑黢黢的,一入夜父母就把我锁在了屋子里。插上取暖器,打开电热毯,西头房里顿时暖和了起来。父亲戴着眼镜,剥着炒花生吃,祖母颤颤巍巍的坐在小椅子上,陪我们看半晚上的春晚,然后早早去东头房睡觉。那个时候我们挤在一间又小又破的屋子里,那个屋子梅雨时节会返潮,墙壁上的漆会一块一块剥离,暴雨时会漏雨,各式各样的盆子都丢在各处,滴滴答答的。然后我们关了灯,抱在一起睡着了。
家里旧日里发过水灾,祖父就挑了许多河泥在岸上,堆出了我们家的地基。再后来过了许多年,父亲从别处找来了许多红砖头,给门前铺了一条路,一条红色的可以小跑下去都不会踩上一点烂泥的路,一条可以直接从下面骑车到院子中间的路。
每次探望完祖母,离开的时候,我都会坐上父亲的摩托车,被父亲裹在他的军大衣里。而我总会挖开军大衣的纽扣口,窥视着外面。我看见祖母站在红砖的尽头一直在那里眺望着我们,直到祖母被小林子遮住了,再也见不到。
我突然发现我可能是在怀念那间小屋子,怀念祖母与院门口的两棵桂花树。他们在我最恍恍惚惚的年纪里,对我挥手告别。我想我应该做些什么。
父亲开车送我去车站,这一次母亲也坐在了里面。从岔河街到淮安东站要两个小时,路上几乎都是农田与低矮的建筑。去年我拍摄的高高的烟筒还矗立在那里,我想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都会待在那里的。整个苏北的农业生产中心都坐落在这里,我的城市巨大也空落。
父亲还是穿着他那件蓝黑色的旧棉袄,戴着眼镜,坐在前面小心翼翼地开着车。母亲将座椅放低,躺在上面披着毯子休息。到站了。东站里面的人员来来往往,母亲和我下车,不放心地一路跟着我,直到车站的入口。她不断地和我叮嘱着叫我好好锻炼,注意身体。一直到我过了安检,走到了向上的自动扶梯上。我回过头才看见母亲在高大的玻璃窗外侧身离去的影子,母亲个子不高,在人群里穿梭着,艰难地在冬天的阳光与风里往父亲和车走去。我觉得母亲也在慢慢地走向祖母。
我终于坐上了去西安的高铁,戴着厚实的口罩,身上缠满了母亲硬塞给我的大包小包。我一路上望着车窗外的山野与农田,村落与高楼,风车与烟筒。烟雾笼罩着整个郑州市,远方的远方是起伏的绿潮。
我就这样一直趴在车窗上望着,目光呆滞又涣散,一直到阳光也不再透进来。
我觉得寂寞了,就从口袋里费力地取出来耳机,听起来了歌:
“那一年我七岁,母亲和我说:去交些朋友吧,不然你会孤独寂寞。
那年我七岁。
十一岁那年,我吸烟与喝酒,父亲对我说:找个妻子吧,不然你会空虚无助。
那年我十一岁。
二十岁那年,我的故事广为流传,黎明还未照耀前,孤独的我无人相伴。
…….
很快我就年过花甲,我父亲也年逾古稀,又一次给老爸写信,他高兴不已。
我希望我的孩子偶尔也来看望一下我。
那年我七岁,母亲和我说:去交些朋友,不然你会孤独寂寞。
那年我七岁。”
我听着歌,突然眼泪就留了下来。人生不过就是一场漫长的告别罢,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