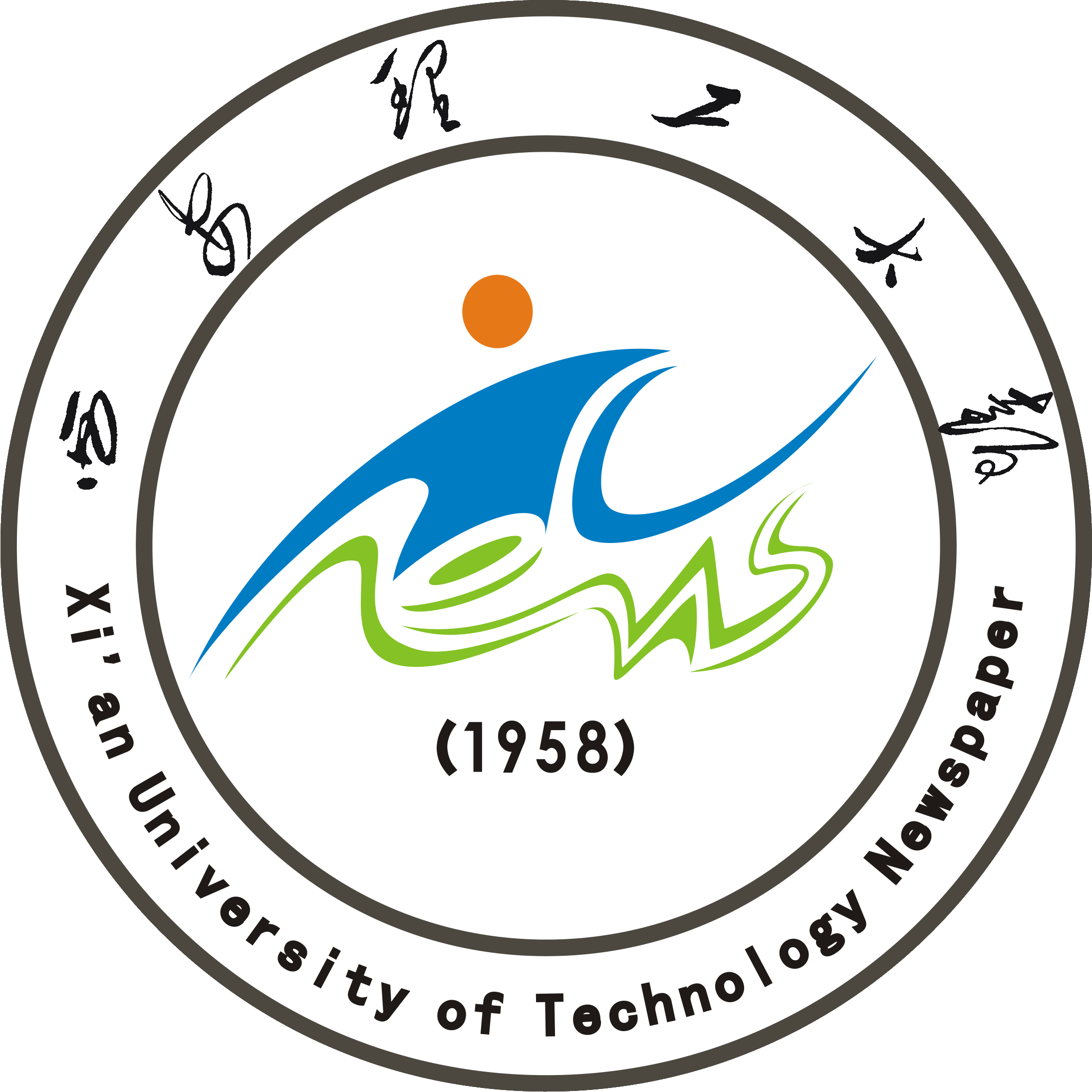有段时间老是爱读一些描写女性活动的书,《伤心咖啡馆之歌》也是在这个时候看到的,仅仅用一个晚上,就读完了,却在随后的这段时间,反复读了好几遍。
我在读完合上书的时候,静静凝视封面上的这个女人,头发有些凌乱,用她那大而深邃的眼睛直直的看着你,目光中带着谜,毫无修饰,却欲说还休,看穿一切却无动于衷,嘴角有深深的纹路,下巴倚在手腕上,手指夹着一支烟。仿佛在说,这就是你们的命运,我只是告诉你们,并不在乎,也不关心。
原来眼神才是一张图片的灵魂,就像爱因斯坦那张肖像照,那双眼睛里蕴藏着一整个宇宙,以至于其他的都微不足道了。也许一个孤独的女作家的真实状态就是如此,不做过多修饰,却用自己柔弱的笔触,将这个世界层层剥开,让你看到伪装着的一切,不论你是否喜欢。
在《伤心咖啡馆之歌》里,孤独却自立的爱密利亚,佝偻而滑稽的李蒙,充满复仇怒火的马文·马西,一切都如此荒诞,如此阴郁而沉闷,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来。但仔细静下心来一想,这三个病人,每一个都令人难以忍受,可是也正因孤独——这一种全人类共通的情感,才使得这三个人之间如此畸形的感情,触动了每一个读者的内心。正如书中所说:“过去忽略了的事情,蛰伏在头脑一个阴暗角落里的想法,都突然被认识,被理解了。”
孤独的故事总是从爱情开始,伤心的故事也总是从爱情开始,这家咖啡馆,见证了爱密利亚的一切,见证了她的喜与悲,爱与恨。爱密利亚能干富有,“骨骼和肌肉长得都像个男人”,让镇上的男人都见而远之。但是,本地最俊美的男子马文·马西偏偏爱上了她,因为爱情,他一改流氓习气成为正经人。在仰慕了她两年后,终于求婚了。但是“一个新郎无法将自己心爱的新娘带上床”,结果十天后“她终于把他撵出了家门”。马西再度成为恶棍,并锒铛入狱。
爱密利亚再次孤独的生活,直到某个下午,她爱上了一个相貌丑陋,来历不明的罗锅李蒙表哥。她雪藏了多年的爱心如同开了一个缺口的堤岸,无止境的泛滥开来。为了他,她事事迁就,咖啡馆也是言听计从的产物。但是在马文假释回来的时候,李蒙却一眼就沉沦了,即使马文打他,讨厌他,他依然时时跟在马文的后面。李蒙在爱密利亚和马文马西的对峙中倒戈,他把她打翻在地的那一刻,她就永世不得翻身了。马文和罗锅偷了她的一切财产,毁了咖啡馆之后逃之夭夭。幽闭的爱密利亚只在每天下午三点钟从一扇小窗户朝罗锅离去的方向,用发灰的斗鸡眼凝望一个钟头。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之后,这窗户,如同爱密利亚的心,再也没有打开过。
英俊的浪子爱一个怪癖的女人,而女人却爱一个丑陋的罗锅,罗锅却倾心于浪子。这段畸恋,“被爱者仅仅是爱者心底平静地蕴积了好久的那种爱情的触发剂。每一个恋爱的人都多少知道这一点。他在灵魂深处感到这一种爱恋是一种很孤独的感情。他逐渐体会到一种新的、陌生的孤寂,正是这种发现使他痛苦。”“正因如此,我们大多人都宁愿爱而不愿被爱。
几乎每一个人都愿意充当恋爱者,道理非常简单,人们朦胧地感到。被人爱的这种处境,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被爱者惧怕甚至憎恨爱者,这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爱者总想着把他的爱者剥得连灵魂都裸露出来。爱者疯狂地渴求与被爱者发生任何一种可能的关系,纵使这种经验只能给他自身带来痛苦”。爱密利亚因反叛马文马西对她的爱情而背叛了他,而罗锅对爱密利亚的背叛当然也就成了罗锅反抗爱密利亚的必然。
対爱情的畸形接受,总胜过对爱情的彻底绝望,爱着很多人也被很多人爱着,在孤独的洪水中拼命地要爱一个人象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于是孤独不仅成了爱密利亚爱情的基础,也成了她爱情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使爱情中的权力意志触发出的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有了一种宁静之美。小镇本身是沉闷的,寂寞的,忧郁的,像是一处非常偏僻与世隔绝的地方。宁静是一种孤独的味道,爱情出现时或许曾是美丽的,就好比孤独的夜中温暖的咖啡馆,也就有了那种被咖啡的苦涩和酒精的诱惑发出的亢奋和骚动。我们无法治愈扭曲的爱情造成的伤害,但伤害并不是孤独的一切,不幸的结局是真实的孤独也是必然。
八月的下午,路上空荡荡,尘土白得耀眼,头顶上的天空亮得像教堂的玻璃窗。枯坐在百叶窗旁的女人,倾听着来自大地深处,被束缚者的歌唱。对麦卡勒斯而言,孤独可能永远与自己为友,但常常也与自己为敌。在《伤心咖啡馆之歌》中孤独正缓慢的宁静的释放着——要想爱的人,孤独是常态;不想爱的人,快乐是常态。这些都是孤独的陈述,都是灵魂的空缺。
本文获第八届读书观影有奖征文活动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