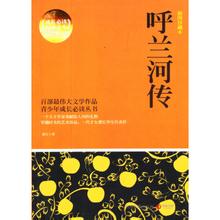
如果你未曾看过她如昙花般绚丽绽放的生命姿态,就不会为那凄美而短促的凋零扼腕叹息;如果你不去体会她命运的动荡艰难,就无法被那一份纯真执着深深打动;如果你不曾了解彼时家国的困苦与战乱,就无法想象她的情怀与勇敢如此难能可贵。
她便是萧红。一位飘然独立于世的伟大女子,一位用血泪歌唱生活的达观勇士。
在我心中,她是一片红叶,每一个文字的书写,都是一段随风的舞蹈,用自己漂泊的姿态,惊艳了岁月的长河。她是一滴泪水,每一次落下,都是如泣如诉的动人诗篇,当我们用掌心接住时,连自己的心扉都变得柔软而深情。她亦是一团火焰,引领者我们走进苍茫的雪地中,却依然能看到光明,被冰封的灵魂便被缓缓点燃。
第一次被那团火焰点燃,就是那部《呼兰河传》了,那一幕幕发生在二十世纪,她的家乡呼兰河小镇的真实故事,那些曾经出现的人与物均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她用毫无造作的语言,和天真直率的性情留下了永恒的热度。
当这个春天的一个午后,我重新拾起这部小说时,便像嗅到古画的墨香一般,回味无穷,却也有了新的体会,更觉之像一幅生动而丰满的珍贵画卷,呼兰河人们的生与死,甚至那时整个中国的美景与废墟都被描摹出了它该有的样貌,和该有的色彩。
有时这幅画是灰白的,让人感到如磐石一般沉重。
小说以“严冬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大地满是裂着口”为开篇,带我们走进了一个冰天雪地的东北小镇——呼兰河。彼时,那里的“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呈着一种混浊的气象”,街道是“灰秃秃”的,就连人们的命运也是那样灰暗,苍白。最为印象深刻的是那个十二岁便嫁入老胡家当童养媳的女孩(大家都叫她团圆媳妇),因为“太大方,头一天来婆家就吃三碗饭”等事就被婆婆虐待,直至生病,直至最后因为迷信而被热水活活烫死。这样的悲剧看得人触目惊心,本是还在玩耍的年龄,自由却被剥夺,最终连生命也被剥夺,掌握命运,追求自由地生活对那个时代的许多人来说是多么遥不可及。
萧红用灰色的笔调,为那时活着又死去的悲苦人们默哀,也为我们的心灵蒙上了一层尘埃。面对这灰白色的画作,思考着如今这美好的世界是怎样的来之不易,我们又该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珍惜当下的光阴。
而这画作有时却亦是赭石色的,混浊中夹杂着低沉的哀鸣。
萧红多次在书中提到“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住在那里的人们都没什么希望,只是希望吃饱了,逆来的,顺受了”,每当人们生病时多半是请跳大神,人的生死最终只能信天由命,这样的迷信是种惯性,却也是愚昧使然。但最可悲的不是逆来顺受的生活和愚昧,而是麻木二字。当团圆媳妇被热水浇烫时,多少人来看热闹,却也无一人站出来阻止,他们就是鲁迅先生眼中的看客,是杀人的帮凶。
当萧红写下这些故事时,那些画面被绘成了赭石色,人心的混沌,社会的麻木被揭露得无处遁形。作为作者,她在唤醒唤醒人们的善良和对命运的不妥协时,也为自己披上了勇士的铠甲。
诚然,纵使这幅画,被刻上了灰白、混浊的印迹,但最终在明亮的金黄面前,都显得惨淡无形,寻不得一丝踪影。
那一抹金黄便是萧红画笔下勾勒的祖父了,还有那段与祖父生活的快乐时光。萧红幼年丧母,父亲性情粗暴,童年里陪伴她,给她亲情的就只有祖父。祖父去花园里锄草,萧红便跟着。对于她的各种问题,祖父总是笑盈盈地详细解答。在孙女调皮捣蛋的时候,祖父也总是宽容处之。当祖母去世后,祖孙两个人的感情就愈加深厚,祖父总是在深夜里教萧红念唐诗,一直到天明他们都还是不亦乐乎。萧红在与祖父生活的过程中,如此天真烂漫,这样的温情让我看到了世界的希望、善良与美好。而这种单纯而温暖的力量便是小说的金黄,如此闪亮,照着人性,照着前方。
在小说尾声,萧红说“呼兰河这小城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当读到这里时,我感到自己眼前一片模糊,泪光闪动,也想起了自己童年时,祖父与我相处的时光,如今已是一去不返了,更想象到作者在异乡的香港写这段文字时,不仅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还要忍受对故去亲人的思念,她的坚强与真诚让人为之动容。
或许,《呼兰河传》这幅画作不只是灰白,赭石,他还有更多的色彩等着我们去探寻,去体味,去发现她的美。
这美一定饱含萧红秉持文学之梦抵御黑暗时代的坚毅勇气,这美也一定是她满怀慈悲之心洞察世事的人文情怀,更是她用生命书写的那一页页人间百态。
如今,作画的人已去,但她的精神却像这幽幽的呼兰河水,每一个遇见过她的人都会是这流水的一滴,永远随之奔流不息。
而此刻的我只想要踏着戴望舒的脚步,在草长莺飞的人间四月天里,走六个小时的寂寞长途,到她头边放一束山茶花,然后等待长夜漫漫,与之共话海涛天涯。
本文获第八届读书观影有奖征文活动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