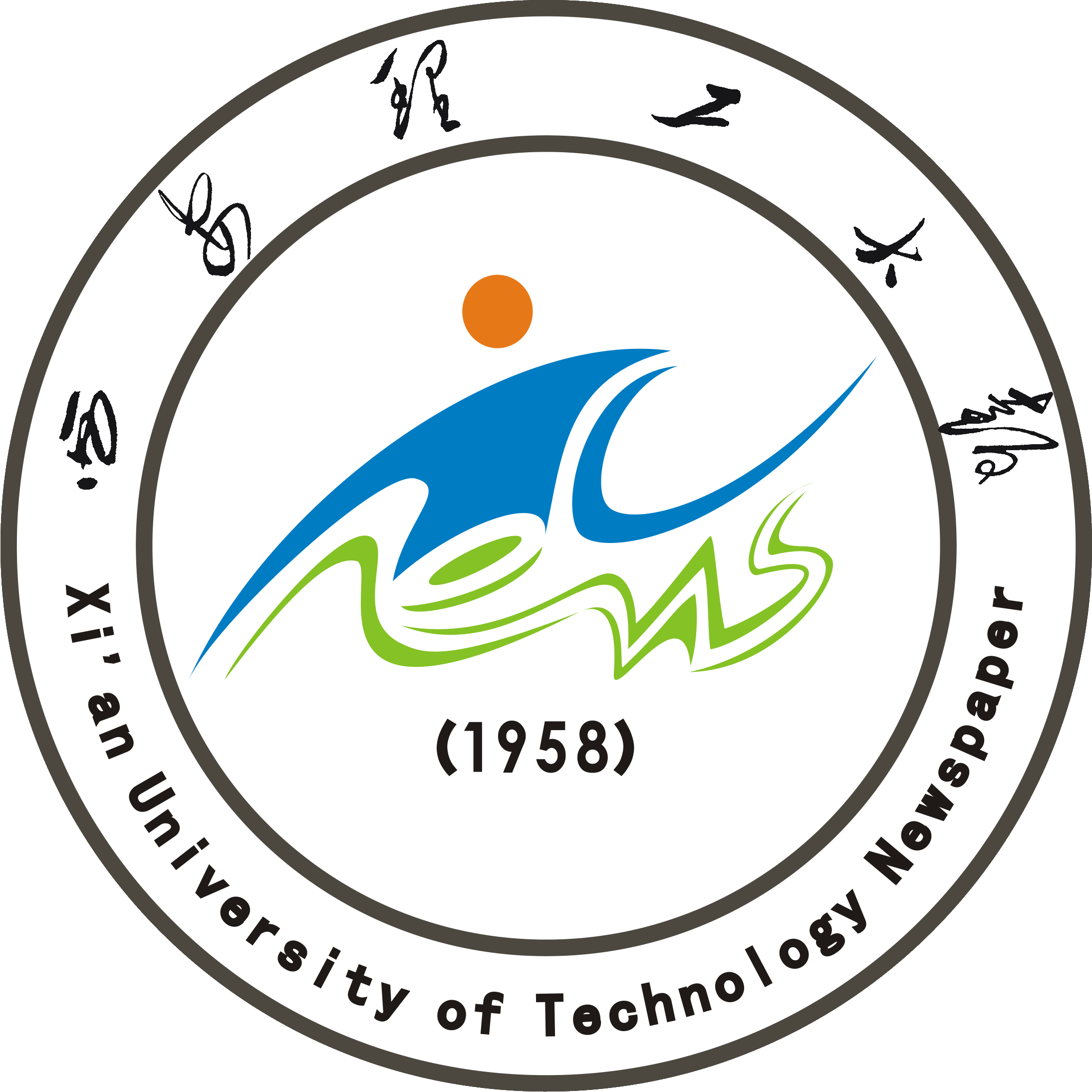我眺望,向着你来的方向,直到我变成了稻草人。不会说话,也不会唱歌。只有一群麻雀陪伴着我,一边吃掉我,一边替我守候远方。他们告诉我,你的名字叫夕阳,可是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为什么,我和你相依为命的家乡变得如此凄凉。
已近深夜的街头,连一片被晚风卷起的落叶也几乎是罕见。可就在那个瞬间,城墙那边的天空升起两簇烟火,有些零星,更有些勉强,好像它们是从往日欢庆时光中被排除的小瑕疵,流放到这个空旷的广场。我站住脚看了一会儿,用了异常大的力气阻止自己像个失败者那样,无法克制与回忆苦苦纠缠的企图。
我在每一次呼吸中留出长长的间隔,让它们盘结成一种势必的魔咒,又用失望堵住了锁眼。安静的走着,用心去抚摸残败的枝条,冬日里的路灯被削去了一半的精神,站的像尊荒山中逐渐败落的神。而我那被剩下的躯体,早已是红土三层,黑土三层,芳草萋萋,牛羊成群了。
其实偶尔静心想想,也对。上帝是公平的,他给你一个能干的自己,就给你一个气态的陪伴——想和他共进晚餐?拿个气球来装吧。哪怕身边人群熙熙攘攘而过,却感觉自己还是一个人。缓慢进入市中心最繁华的街道,两侧的霓虹灯如同神话里那片为摩西而分开的红海,却是要把我送到空旷的绝路。所以往事有什么好提的呢,从来只有失败的人会对过往的美好念念不忘,像抱紧悬崖上那根脆弱的树枝,恰恰让自己的坠落在这番徒劳中显得更加悲情。我怎么肯承认自己的失败。
我总以为需要付出自己百倍千倍努力的,应该是事业,是对疾病的抗争,是对家族存亡的维护,而爱情这种东西,原本也不应当通过努力的途径获得,它应该早就在那了,它也势必会在哪儿。在我出生到这个世界时的第一秒,或者更早,在月亮仍然没有被抛出地球身体,宇宙还在安排各种内部的运行轨迹时,便已经等在那里了,只看我什么时候遇见,什么时候领它走。
它是唯一被命中注定的东西,所以,我急什么?我怕什么呢?我有什么可害怕的,有什么可担忧呢?就像一个自由落体的皮球,是无法靠什么自身的努力来改变下落的趋势的,唯有等待外力出现,那冥冥中,欣欣然的一双掌心吧。他来得着实有些晚,他来的姗姗又姗姗,让我不得不怀疑——我像被无数泡沫哄抬着上的船头,高高的在波涛中扬起最后重重的摔下那样不得不怀疑,也许他根本就不会出现,他根本就不存在。
来到我的高中校园,它看起来有些荒芜了,但它看起来又是俏皮的,好像一个不懂装扮,只凭本质在倦怠的十六岁的少年。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栋灰色的建筑会让我产生这样唐突的想象。但至少在那里,我有一切想要的东西。疯疯癫癫的穿过大街小巷,毫不避讳的放声高扬。是谁残忍的带走了这一切。现在的我很清楚才对。我很清楚自己用实则关了一扇门的姿态开了一扇窗,迎着我的眼睛吹来的风,很干净,没有沙尘,但它们充满了放弃与失望的气味,已经足够在眼角熏出一些懊悔的潮湿来。三三两两的并肩走过,空气中都充满浓浓的爱意的芬芳。看起来,她们似乎是战胜我的,她们在一场并不起眼的战争中打败了我。这番胜利即便谈不上振聋发聩,可依然不影响它的温柔效力。毕竟他们没有在十五岁时过早的相遇,也没有等到三十岁还迟迟的陌生。他们的恰到好处就是被世人称之为缘分的东西吧。
现实,这个词有着强大的氧化作用,会很轻易的让某些稚嫩过往变得面目全非。大家都离过去太远了,很难想象曾经的情愫在今时今日还能捕获我们。它的力量原本就单薄,仅能粘附年轻时天真而荡漾的物质,比如心,肩膀,断发或剪影。
我不难过,自然没有悲哀,只是迷茫着,迷茫像晨雾般伪装了有限的意识,让某些暂时按兵不动的要素开始了酝酿,那么它迟早要在未来成为毁灭性的武器,它会狠狠地握住我的心脏,在里面攥出溃败的恨和痛来。也许这个年龄,达到这种层次,是不该在迷茫的。剩,而又如此。只有在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打击之后,才能够练就一副金刚不坏的身躯。有了这些,今后的道路会不会更顺畅?
他在离我近在咫尺的地方,一切一切却像走廊里的灯光,白色,平板而形式化。从来没有什么爱情故事是在这样的光泽下发生的吧,它们理当属于夕阳,霓虹,星光,或者烛火吧。一点儿呼吸的变动也将带动气流影响它的闪动,飘忽的灯焰象征女主角那个动心了的瞬间。我渴望的,我追求是我那些,需要动用到灵魂,感觉这类词语的追求,它们纠缠在内心深处,宛如一株集聚了神灵的槐树,将在满月的时候召唤来萤火——但对别人来说,它只是棵平常无奇的木头,遇到了严苛的冬天就要不容分说的砍伐了取火。反复的。反复的。锯条渐渐地从我胸口割离那片绿荫。好吧。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二十岁出头的时候,真爱至上不是笑话而是神谕。它就应该被纯粹而有力的火光燃烧,反复地出现夸张的画面都没有问题,谁也不会责备,哪怕奉献上生命,最后都能被理解。时光将我们那一份热情磨平,淡化。但并不因此使我们失去信心。一点点的累积,一点点的铺就成我将称王的道路。
这一切的风霜雪雨,一切的苦尽孤独都是通往成功的一道道考验。熬过去,君临天下。受不住,平凡一生。我当然会孤独,会寂寞。当凡庸的世界用温和的侵蚀同化了我,那一刻我会希望至少身边有个人能够见证我的碌碌无为。打出去的电话,没有人接通,久久的等待后,宛如测试一个无底洞的深度,告诉着我,哪怕投进整个生命的长度,也唤不到半点儿的声息。
安静久了的人,更是应当走去欢腾的地方闹闹。让心也感觉到自己的跳动才好。球场就是这么一个不错的选择。人群在四周随时爆发出的喝彩声,好像一场节庆的烟火。当一切介质都在传递着猛烈的欢呼,它传到我的脚底,将一把掌声塞在我的手里,随即它们开始温热的扩散,让我意识到自己有一部分被同化,我被鼓动着,像在狂风中不能站稳的双脚,而它们站在快乐的波涛上。也许看开始比劝说更好的一味良药。
我意识到我其实一直是挂着微笑的。好像等待出场的衣服,天天被拿出来精心熨烫一番,最后又落寞的回到柜子里。到最后,我俨然能摸到内心在一次次炙烤后烧焦的卷边。这一切看开就好。剩,也许更是值得人去深思的艺术。一路顺顺当当的走过,是所有人的一种愿望。更应该说是奢望。它既然被人们赋予了如此高贵的评价,那自然如凤毛麟角少之又少。没有孤独一点点的撬开成功的大门,又怎么会有你称霸天下的那一天。我更愿意把剩理解为一种等。
在漫天飘零的梧桐叶下,我在路的尽头等待,希望你的面庞能在一片片梧桐叶落下之后变得渐渐清晰。永远不能彻底的根除它们了,不论多少次撕碎它们的翅膀,它们是落在盐晶上都能生根的种子——我自己心里,对爱情的向往,是它点燃了,它是见到火就要扑的,它是能够直接穿越我的身体的,我根本无从阻拦。
我希望自己是成功的在脸上展开一幅无谓,一副释怀,甚至是一副逆转性的戏谑。我像面对上千错乱的拼图,慌乱的企图完成一个笑容,让它如同一滴墨水也要将整条河流染黑那样,在自欺欺人的意图里再度摇头。有些话,有些意图,有些努力和尝试,成功了便是羽毛是雪,衬上诗词和曲谱,一派可被装裱的美丽。但假如失败了,它就是满载难堪和懊恼的路碑,将永永远远记录你曾经有过那么孤注一掷却颜面尽失的败北。
我不怕别人议论我的特殊,我一直在等。哪怕最后满头白发回忆这个被剩下的一生,也不要在夕阳落下之后后悔当初的决定。我不肯屈从于任何有损梦想和爱的现实,我要的一切都会弥足珍贵。既然爱情,理想已经沦落成地球上的最后一件奢侈品,那么我能做的,就是拼死坚守这个珠光宝气的橱窗。
我是剩者,是被这个时代所抛弃的人。
我是胜者,是将要站在巅峰统治的人。
我更是圣者,是已经恬静看待一切的人。
本文获第八届读书观影有奖征文活动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