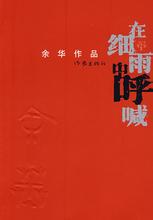
李商隐在《锦瑟》中写下了这样的千古名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其道出了对追忆的回味无穷及惆怅至深;人们通常都认为在人生的旅途上走的越是长久,收获的便是更多,而李商隐则真实的感叹了出对于回忆在当时就有惘然之感。
《在细雨中呼喊》也是一本回忆童年的作品,小说徐徐展开了碎碎叨叨的记忆,重温了作者年少时期对生活的感受和理解,其故事荒诞而又令人心碎,将读者带入了寓悲伤于幽默的特殊意境之中,这种意境随着作者的描写悄然渗入心底,之后,又随着人物的描写渐渐消逝了。
主人公孙光林有着被动的放逐和回归经历,两个家庭的生活使得他的童年境遇波折坎坷,触目惊心的故事也是接踵而来,被抛弃之后又小心翼翼的承受着关怀,被遗忘恍惚将有又那份真挚的救助,而就是在这似乎无情却有情的现实里,童年的苏光林在慢慢的成长;大致是因为看着小说之中的主人公的抛弃遭遇一次次被作者用笔轻松的述写在一页页纸上,那种悲戚的伤感便不会那么轻易的从我的内心涌然起来。
美国《时代》周刊对于这本小说引出了这样的哲学思考“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土地上,事实上我们生活在时间里”;有时候我们会追随消逝的岁月,回味那些走过的年华,就在不经意间,时间便是从我们的追忆中溜走了;当我细读《在细雨中呼喊》之后,有种生活在时间绽放的丛林之感,被繁茂枝蔓紧紧包裹着,即使刮风下雨,我依然被牢牢的保护着,呵护着;而孙光林在童年的时段里却在生活的细缝里呼吸,孤独的寻找着依赖和关怀,他在最敏感和孤独的时候,身边总是发生着一些荒唐的故事,而他自己总是被忽略,被遗忘;在这个人性的弱点被扩大的环境里,带给他的是对幼小心灵的侵蚀。
“试图以一个句子终结一个事物的语言”是余华的自述写作特征,他以最为轻松巧妙的写作方式,将各种人物活跃在纸面上,而这些小说里的人物编织在幻想和现实交错的环境里,内心的矛盾和纠结将其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最终的结局,便是用最为简单的一句话了结了,仿若存在的人就该如此般黯然消逝;小说中孙光林的母亲故事让我难以忘怀,她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有着勤俭持家,善良朴实美好品德,然而她的美好被一步步摧毁在丈夫的荒唐行径之中,她在容忍和矛盾深化的极致时,便带着怨恨和委屈离开了人世。
“这一刻我清晰地看到了她遭受岁月摧残的脸,脸上的皱纹已经清晰可见,她那丧失了青春激情的目光看到我时,就像灰暗的尘土向我漂浮过来”这是小说中另一位曾经拥有青春美好的女子,在生活的摧残下变得沧桑后的描写,可以看出,她不仅丢失的珍贵的岁月,也丢失了灵魂,麻木的生存着。
困苦的生活往往造就了经典的人物,在困苦中,曾经被隐蔽着的真情或者自私将毫无保留的被呈现出来,像《平凡的世界》一样,这本小说中也有着艰难的生存环境,人们为生活而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耕作,并要学会淡定从容的接受时光给予的劳动成果。
像这样,作者精心安排了乌云密布,然后下起了连绵的“细雨”,被“淋湿”的那些人,在呼喊。
我想,我不能体会在细雨中呼喊的感觉,那是肆意的发泄,还是对未来的祈求?
我也不知道该以怎样的姿态行立于这篇深长的故事之中,怎样去触摸和探索人物的灵魂,呼唤出被书页尘封的气息,然后在我的脑海里展开一幅如清明上河图般的人物画卷,千姿百态的画卷。亦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诸多人物的凄凉境遇,所以只能轻轻地叩开深蓝的门扉,悄悄的走进去,听他们诉说着,看他们与生活争斗着,终于,随着他们的消逝带着万分感慨落寞的走了出来
我渐渐的发现,我不是在读书,而是在品一段人生。
文字赋予了故事的灵魂,走过字里行间,便就路过了一段传奇,一段辛酸的人生之路;也许就在我痴意这些太过普通的文字时,不经意间便成了小说的主人公,走着早已书写好的路,熟悉了那些陌生的人,徜徉在不受时间和空间约束的虚拟生活里,体验着自己从没有体验过的生活,接受着不愿接受的命运安排;于是,我便有了所谓的百感交集,带着文字所拥有的那份独特情感诗意的活着。
本文获第八届读书观影有奖征文活动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