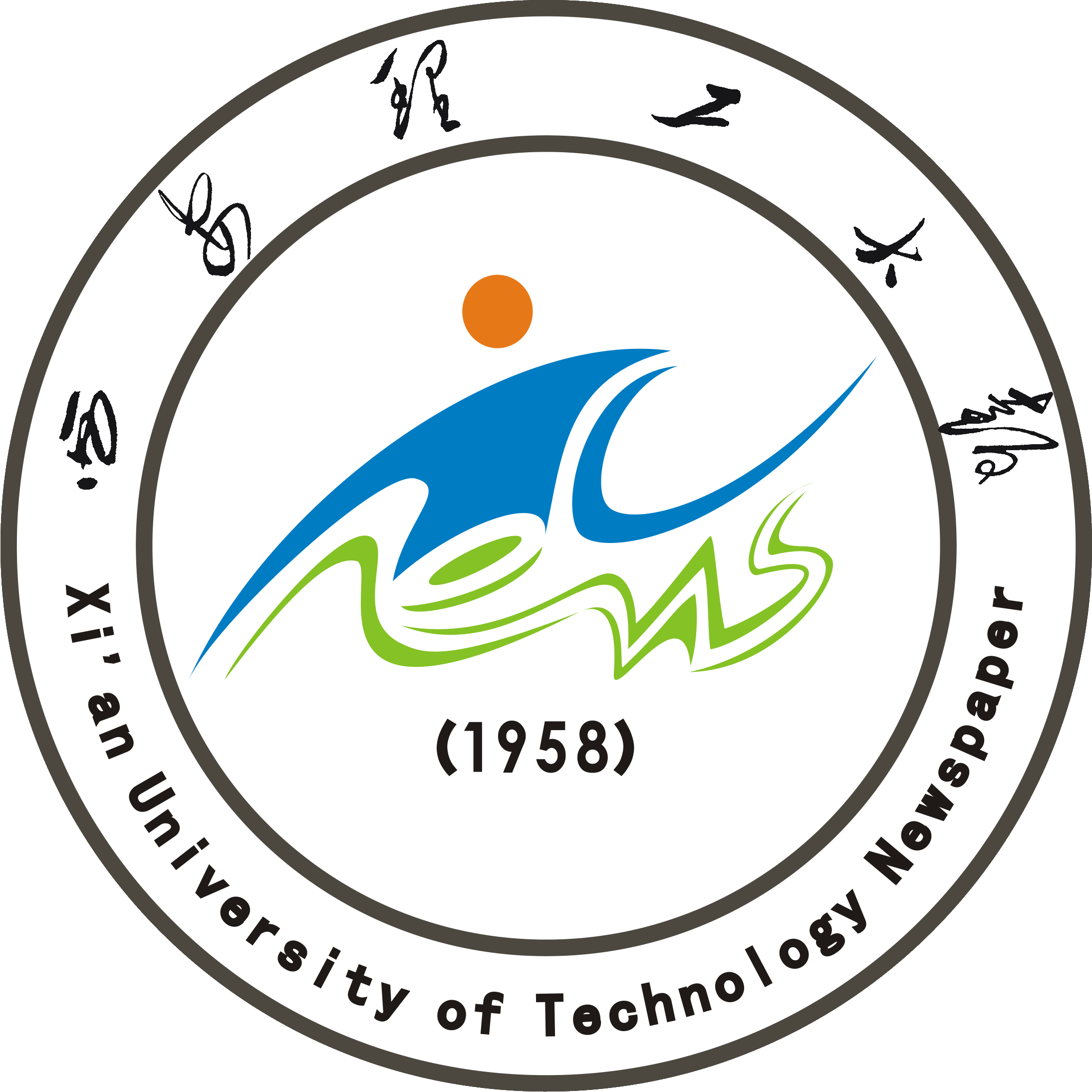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曾拥有,正在拥有或者将会拥有一份不分贫贱,无关年龄的温情。这份温情隽永的像是我们身体中从一辈一辈人那里延续而来以后不知还会延续多久的血脉,大多时候看不到却实实在在温暖着我们。
然而,大多数这份温情的给予者却没办法跨越生死陪我们走过我们二三十岁以后的岁月。他们戛然而止的消失让已经习惯他们存在的我们常常在看到曾经他们夏天里握过的蒲扇,冬天里端过的茶缸时心里除了萦绕着“爷爷”或“奶奶”这两个称呼外,还有种类似想念难过的感觉在骚动。
《飞越老人院》中那些来自不同家庭并且经历身体心理生活困扰,在老人院中结识,一起面对儿女的冷漠,一起自娱自乐,一起谋划逃出老人院,一起跟院长“斗智斗勇”的爷爷奶奶们只是这个庞大群体的一个缩影。
我们常说,岁月是把杀猪刀,这把刀作用在爷爷奶奶身上的直接效果就是败坏了他们身上的一切零件,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借助牙套,助听器,老花镜,拐杖甚至尿管这样的装备来武装自己。这些装备强大到可以帮助他们进食,可以帮助他们在听别人讲话时不至于总是让对方重复所说,帮助他们走路不撞到桌角,甚至帮助他们代谢食物。
这些装备显示的功能越强大,证明爷爷奶奶活得越无力,越艰涩。装备很遗憾地忘记让爷爷奶奶能保持好的记忆力,因为他们老是手里拿着空杯子站在水壶面前想自己要干什么,因为他们经常拿着钥匙心力交瘁地满屋子找钥匙,因为他们也经常站在楼梯中间想自己该上去还是该下来。装备很抱歉地不能充当爷爷奶奶身上的消音器,因为他们不说话时嘴里照样能发出很多声音:不利索的咳嗽声,粗重的喘气声,夜里雷鸣般的打鼾声。装备当然也很欠揍地不能帮他们免疫因吃任何稍有刺激性食物所带来的病痛;太辣的,上火。太冷的,拉肚子。太甜的,胃作酸。太油腻的,没准儿高血脂。大小便失禁问题直接将他们推向更尴尬的境地,止痛片永远是床头不换的伴侣。
这样的爷爷奶奶就真真正正地活在我的身边,六七岁相信故事的年纪,觉得他们是天上地下最会讲故事的人,十五六岁开始按自己喜好交朋友的时候,觉得他们是天底下最无趣琐碎唠叨的人,二十岁左右了解老龄人群时,觉得他们是最需要被爱和最缺被需要感的孤独的人。
家里的饮料瓶子,废旧品,都是他们收集要卖的;饭桌上不准浪费粮食,都是他们要求的;屋里烦的想撞墙的我,都是他们追问成绩闹得;不过,兜里每个月一笔可观的零花钱,也都是他们背着父母偷偷给的。我也很不好意思的发现他们开心的理由其实很简单:一双过冬的棉袜与拖鞋,一包不贵的冰糖与奶粉,一碗端到他们手边的米饭,一次心不在焉的聊天。
我们学步时扶着我们的人现在得抓着我们才能迈过那个不高的门槛,曾经包揽家里大小事宜的他们已退居二线,当起了“甩手掌柜”。在他们没有足够精力频繁甚至直接地参与到有朋友圈,有微博,有游戏,有逛街,有考试,有聚会的我们的生活中时,他们所能想到的亚频繁曲线救国式的参与就变成了这样:一罐跋山涉水快递而来的辣椒萝卜让几个宿舍的人欲罢不能直呼过瘾;星期必须报备近况的电话挂机时总觉得他们似乎还想再说点儿什么;交代后事般地把存折的密码说出来怕自己活不过明天。
龙应台说过孩子与大人的关系无非是一段目送,大人看着小孩渐行渐远的背影对他们说“不必追”,小孩看着大人踉踉跄跄的背影对他们说“不要追”。开始痛恨那些把爷爷奶奶当成一种唯恐避之不及的负担扔进养老院的做法,开始后悔以前自己对他们的各种不耐烦,开始在他们因失去他们另一半而变得对死更敏感时,说话不在口无遮拦,开始在他们靠着在记忆里取暖度日时,安静地坐在他们身旁听他们将那过去的故事。
他们转山,转水,转佛塔,来到我们身边做了一世的爷爷奶奶,完美型的也好,唠叨烦人型的也罢,无论接不接受,不变的温情不减不退,喜好健身型的也好,爱养花种菜型的也罢,无论喜不喜欢,不变的温情只来不去。所以请珍视这样一圈人:他们来过,存在,或者将会来。
本文获第七届读书观影征文活动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