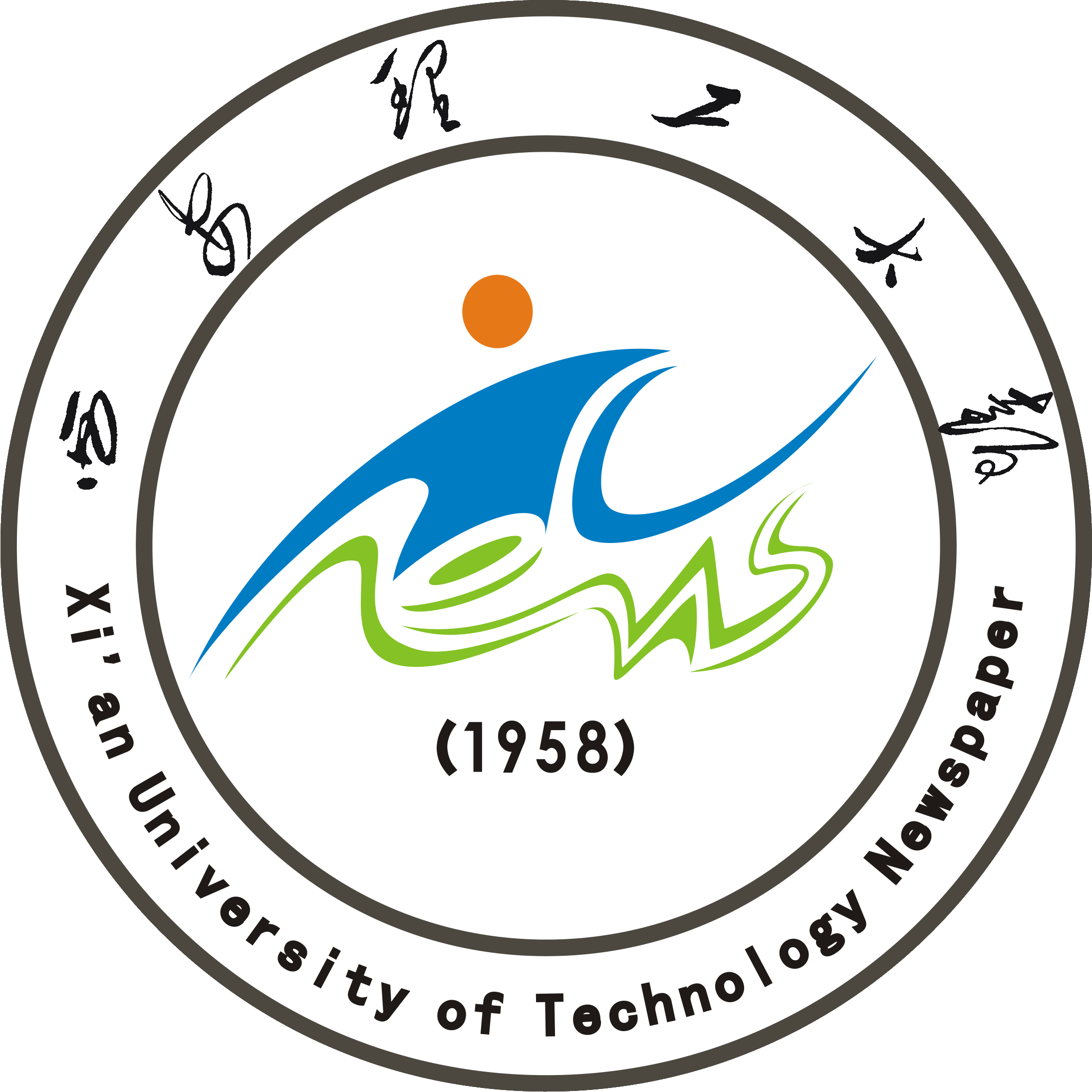由于疫情原因,今年的清明节我是在西安“过”的,这是我在世二十九年来第一次清明节不在家,也便没能吃上那口母亲亲手做的香椿,小时候对于香椿的喜爱不是很深,长大后随着肉体与故乡在空间上的抽离,爱意在逐渐加深。
记得去年清明节母亲骑电摩将我接回家,道路两旁油菜花开得很是鲜黄,含苞待放的洋槐花弥漫着淡淡的清香,香椿的春芽正是绿的时候,乡村的春天是城市无法比拟的。今年身处城市的我打视频向母亲说了清明节不能回家的歉意,母亲像往常一样泰然自若地说:“我娃的心妈知道,回不来就不回来了。”
我的内心还是有些难过的,从正月初四来西安,因为疫情,已经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没能回家。疫情给人们带了很多麻烦,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人员流动,生活中多了一些困顿的人,而困顿之于我,就是在清明节没能回家上坟,没能看望母亲,没能吃上母亲做的香椿。
知儿莫若母,母亲总是能理解儿子、体谅儿子、宽慰儿子。“你大(爸)回来上坟就行了,香椿都给你掰好了,我再给你蒸些馍,让你大去西安了给你带上。”4月9日,父亲返回西安,我吃上了母亲掰的香椿。
取几撮香椿过一下开水,墨绿色变成了新绿色,这种绿不是麦子的青绿,也不是柳叶的嫩绿,好像没有一种植物可以比拟,香椿在开水中褪去了那层“老气”,春天的气息填满了整个厨房。“过开水”这一动作母亲今年再三叮嘱,说香椿含有亚硝酸盐会致癌。我知道微量的亚硝酸盐是不会致癌的,但母亲的话我还是照做了。
碗中打三个鸡蛋,将剁碎的香椿融入其中,加入微量食盐,搅和均匀,热锅凉油倒入,轻微翻炒,待鸡蛋变色便出锅了。出锅的时候,我知道这次香椿放多了,成了“香椿炒蛋不要蛋”。究其原因:一是对于香椿的怀念达到峰值了,二是一年多没做过香椿炒蛋拿捏不住量了。后者原因我想了想,觉得不充分,母亲间隔一年做的香椿炒蛋并没有出现香椿多了或是鸡蛋多了。
有些惭愧地对娇说,香椿炒蛋炒坏了,香椿确实放多了。娇说她之前没有认真地吃过一次香椿,这次吃了之后,就爱上了,香椿越多,她感受到的春天越多。我心中暗喜:“我和香椿一样,见过一次,就被你爱上了。”吃前吃后各拍一张照片发给母亲,吃前是为了向母亲“炫耀”自己的厨艺,吃后是为了说明香椿的好吃。
母亲还向我介绍了香椿的另一种吃法:油泼香椿。香椿过完开水过凉水,捞出用手挤压出水分,切成沫状,撒上食盐和面面辣子,热油泼洒,搅匀即可食用。母亲的做法透露着八百里秦川上劳动妇女的简约与质朴,没有花哨的食材与调料,却用那一勺热油泼活了整个春天。
香椿随着春天的来临,发芽、茁壮、变老、凋落,母亲也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慢慢衰老,对于香椿来说,年年都会有春天,而对于母亲的人生,能有几个“春天”?答案是就只一个,却全部奉献给了我。母亲今年整五十岁,到了人生的“秋天”,本是收获的季节,她却仍在劳作着。母亲说她准备今年干完收羊奶的工作就不干了,我高兴明年清明节不能回家的时候可以吃上母亲做的香椿了。
母亲和椿,皆是我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