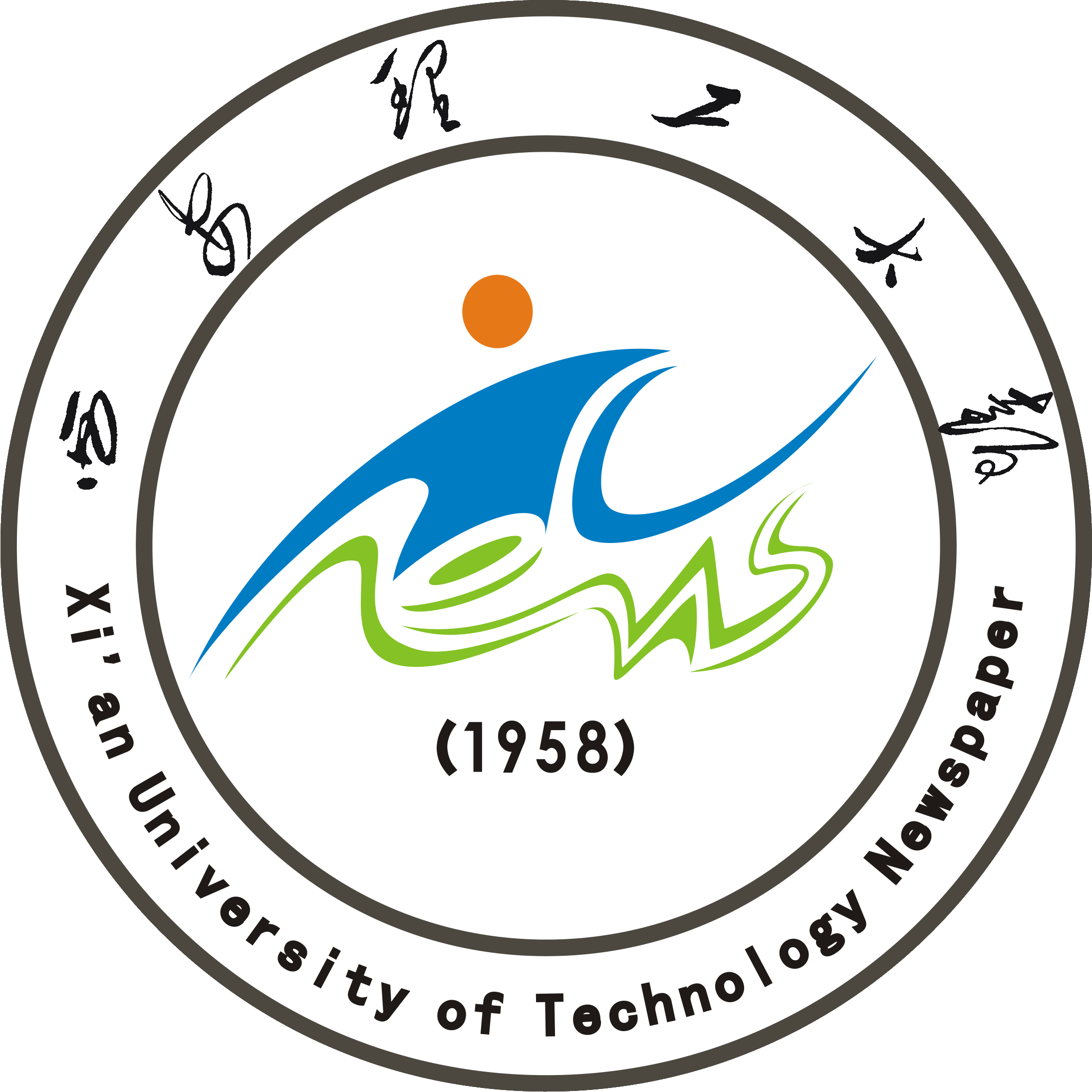21世纪00年代初的风夹杂着从外婆簸箕上洒落的稻穗和我跑过田野边扬起的尘土。风吹过傍晚的天空,晕染开了粉紫交错的晚霞,像米开朗基罗把所有迷幻的想象全都泼洒在画布上,勾勒出了我那个年代特有的颜色。
抓住20世纪的尾巴出生的我,从我记事起的时间轴就是始于21世纪00年代,那时候的我爸的脸上还没有纵横的沟壑,我还有一双天真的眼眸,时光平静的像是奶奶的摇椅,缓慢摇动,却没有荡起一层风浪。
小时候,爸爸的工作是当一名摩托车司机,在那个交通还不是很发达的年代,催生了像我爸这样的靠摩托车载客谋生的摩托车一族。爸爸总是早出晚归,想在我们农村里拉活是养活不了我们一家的,所以爸爸得进城去。在我妈的嘴巴里,爸爸的工作经验相当丰富,他跟着大船到海里捕过鱼,也曾背井离乡到外地打过工,所以进城拉活对于我爸而言好像并不是一件难事。每天早上爸爸发动摩托车,风吹起他的头发和衣角,踏着清晨的露水,驶过瓦砾平房,穿过乡间小道,渐行渐远。每天晚上我和妈妈只要听见那个熟悉的摩托车发动机的声音靠近,呼啸着风声,我们总会默契地说:”爸爸回来了。”
妈妈是她的兄弟姐妹里最大的那个,从小她就承担起帮助外婆干农活的任务,每当夏末秋初,妈妈就会拾起镰刀,去外婆家的稻田里收稻谷。我肆意奔跑在田野间的小道里,小心的迈过一个又一个的沟坎。风吹着田里的稻穗,涌起一层一层金黄海浪,吹起田边的稻壳,穿过妈妈发梢,传来收获的气息,夹杂着妈妈的发香。等到秋末,山林间覆盖了一层落叶,妈妈又会拿起他的镰刀,到山林里去砍柴拾柴。秋末的天空蓝的像婴儿的眼睛。跟随着妈妈的脚步,越靠近山顶,天越蓝,风也会越大,吹的树林间沙沙作响。有时候一阵稍大的风,就能将边上腐败的树枝抽断,因此我总是能听到时不时从山林间传来树枝折断的声响。妈妈是个女强人,她可以一口气把两捆比她人还大的树枝用扁担背下山。生活的重量好像也从来没有压弯她,21世纪初的我妈挺拔的像那山上的树,秋末的风再大,也从来不会被吹倒。
那时候没有手机,电脑也还没普及,我所有的娱乐生活除了晚上在家看电视外,就是和小伙伴奔跑在乡村间的各个街巷,从清晨到日暮,和小伙伴们嬉戏打闹。那时候我喜欢追逐穿行过小巷的风,因为风里带来了外面世界的气息,等我追上它,我就能触及到远方。更多时候的2000s是一根冰棍,一首周杰伦,一个溜溜球和一双奔跑的脚。我记得伙伴的眼眸里充满了各个季节的气息,热烈而狂野。在地面冒出第一颗嫩芽开始,将风筝放逐天际,感受春雨滴滴答答。在盛夏爬上树,屏息倾听知了的鸣唱,伸手去捕捉藏于缝隙间的甲虫,靠一根五毛钱的冰棍就能与似火的骄阳和解。在秋末感受微凉的泥土芬芳,追赶像水一样清澈的天空。在初冬踏平“山川河海”,探索乡村的边界和未知,寻找还有生命的动物。一年四季,随风的脚步前行。
之所以对那时候的风抱有特殊的情感,是因为风不同于阳光或者雨露,无论何时各地,我都能感受风的流向,恒古不变的在大地上不停息的涌动。因此它能保留下那个时候我能感受到的生活气息。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化建设,稻田被平房覆盖,乡间小道变成了宽阔的水泥路,车来车往,再也容纳不了孩童奔跑的脚印。父亲的那台摩托车被置于杂货间落满了灰,妈妈的镰刀早已失去了踪迹,山野间的折断的树枝也已无人问津。
当风再次吹起,我依然能闻到属于童年的气味,穿过妈妈的发梢,流动在我手边,触及我的毛孔。风继续吹,吹翻了米开朗基罗的画布,打乱了五彩斑斓的颜料,破坏了他美好的幻想,却没能遮掩我孩童般清澈的眼眸,透过它我看到了属于我的200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