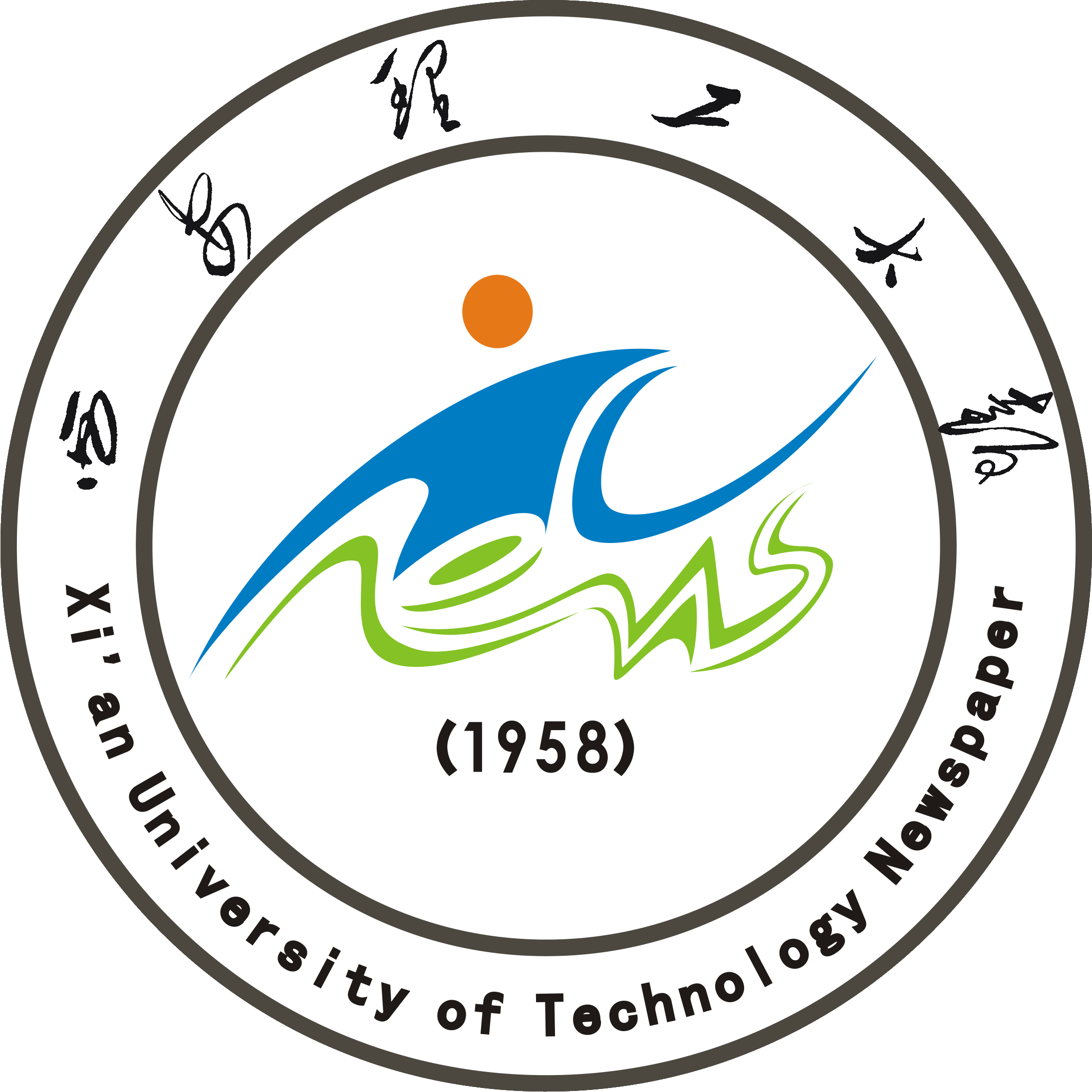人生的本质其实是一场悲剧,喜剧只是慢慢人生的小小插曲而已,更可悲的是有些人的人生连喜剧都不曾上演。心灵鸡汤喝多了也会上火,需要现实的冰冷来平静一下炙热的头脑和浮躁的心情。
还记得那时候我四年级,她初二,在我心中她是一位会下超级好吃的醋汤面、会手工制作各种精美的小挂件、画画一级棒、跳橡皮筋从一级跳到六级都不会坏的天下无敌的大神,是我世界里的偶像,而我就是她的小跟班。
一次去小卖部买盐,当然少不了她和我一块儿,在那间不大的杂货店里一位上了年纪的中年妇女看着铺子,趁我付钱的空当儿,她在货架前转悠了几圈便出去了,等我出来的时候她手上拿了一包零食,我很是惊讶;
“你哪里来的钱啊,怎么买的零食?”
“我没有钱啊,看,小卖部橱窗那儿有个小洞,趁你付钱的时候,老板没注意,我把它从小洞里扔出来了,这样就不用付钱啦!”
她脸上丝毫没有那种第一次偷东西的忐忑不安,取而代之的是平静无奇,似乎是一个行窃多次的惯犯。我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由于我们都是坐落在偏僻小镇的那栋丑陋无比的公寓楼里的租客,对于她的背景我有些了解,从街坊邻居的口中我得知,现在她家的女主人是她继母,当初带着一儿一女来到这个家庭,成为她鳏夫父亲的妻子。像所有童话中的继母一样,她对这位前妻的遗物很是不满,现实版的辛德瑞拉上演了。
那晚,窗外的雨用力的砸着玻璃,似乎想要进入这栋住着三家人的水泥楼。十点多了,爸爸在还前屋忙着修车,妈妈打着下手,后院里,雨声打破往日应有的蛐蛐儿叫,想要掩盖这栋楼里发生的什么,在弟弟的轻微呼吸声中我还不知疲惫的看着电视。
突然,睡房门咚咚的被砸的很响,急促的胜过暴雨砸地,我招呼着“来了来了”,便跑向门口,刚把锁拧开半截,门就被撞开了,推了我一个趔趄,还没来得及生气就反应过来出事儿了。狼狈不堪她的一屁股塌在墙根下的长椅上。妈妈听到砸门声已经赶过来了,冲进来跑到弟弟床边,看见弟弟没醒,给弟弟掖住被单儿,回过头来看到我俩。
而我被吓得在一旁愣住了,而她的样子连我妈妈都惊讶了;
“娟娟,你这嘴上的血……?”
她不哭不闹也没有说话,低着头,抚摸着肿胀的双手。身上皱巴巴的睡裙明显小了,短了半截儿的袖子露出了胳膊上的抓痕,哆嗦的双腿很快将我的眼光吸引到她的小腿上,一条条鲜红的鞭痕煞是醒目。赤脚跑下来的她头发散乱着,嘴角没有擦净的血渍诉说了过去的几个小时她经历了什么。
妈妈没有多问,只是让我去把柜子里的药箱拿来,便开始帮她擦拭伤口,碘酒抹在抓痕上很痛,她只是面无表情的看着妈妈给她上药。往日那个蹦蹦跳跳、天真活泼的小女孩儿不见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经历了太多苦难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了那天我和她的对话。
“娟娟姐姐,别哭了,再有几天暑假结束了你和我去我家吧!我们可以一起画画、上学,我房间可大呢,我们睡在一起!”
“好哇,反正我爸和阿姨也不会管我,我跑了他们不会知道的。”说完吸了吸鼻子,拉下长袖盖住手心的板印。
到现在都不能忘记她当时充满希望的那双眼睛,那是一种饥渴的士兵发现泉水的明亮,而此时此刻的她眼中毫无生气与希望,好像对人世间很绝望,那种骇人的空洞好像能让人切身体会到她的痛苦。
妈妈继续去前屋忙了,她像一匹从猎人抢下死里逃生的小鹿,伤痕累累,默默地在长椅上坐着。我给她倒的水拿的饼干她没动,我也不知道该和她说些什么,只有雨依旧下个不停好像没完没了似的,暴雨让外面发生的一切都有着很好的伪装。十一点的钟声响了,她睁开了眯着的眼睛,像被下了魔咒的公主去触碰纺车的尖针,她从长椅上站起来,如同行尸走肉般朝门口走去,像一个做好准备去为世人承受苦难的修女一样,有无奈、有痛苦、有平静,她的背影消失在房间的光亮中。
在那之后的几天,她很少出现了,作为跟班的我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直到我开学离开的那一天都没有见到她,心里的失落感一直陪伴我到了现在。
后来的故事还是妈妈告诉我的。开学了,她并没有去上学,房东去她家里发现男主人与继母早已打包走人了,留下半个月的房租和孤零零的她,这让房东太太很愤怒,于是把一切都降罪于可怜的她,硬生生的把她从房子里赶了出来。她带着一包衣服无处可去,只有在后院的杂物室里住着。靠着街坊邻居的救济,和新房客的施舍勉强度日。
童话故事里的灰姑娘有仙女教母,她没有;灰姑娘有参加皇家舞会的机会,她没有;灰姑娘最后当上了皇后,而她更没有可能。
几年过去了,我再次从妈妈那里听到关于她的消息是她结婚了,与其说结婚还不如说被人卖了当媳妇,不知道这是她幸福的开始,还是另一段痛苦的开始,无依无靠的她要一个人面对这个无情的世界。
每一个女孩子都是美丽的花朵,都应该受到阳光的滋养,但总有一些地方是阳光不曾光顾的,那花儿只能枯萎。愿世上每一位女子都被温柔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