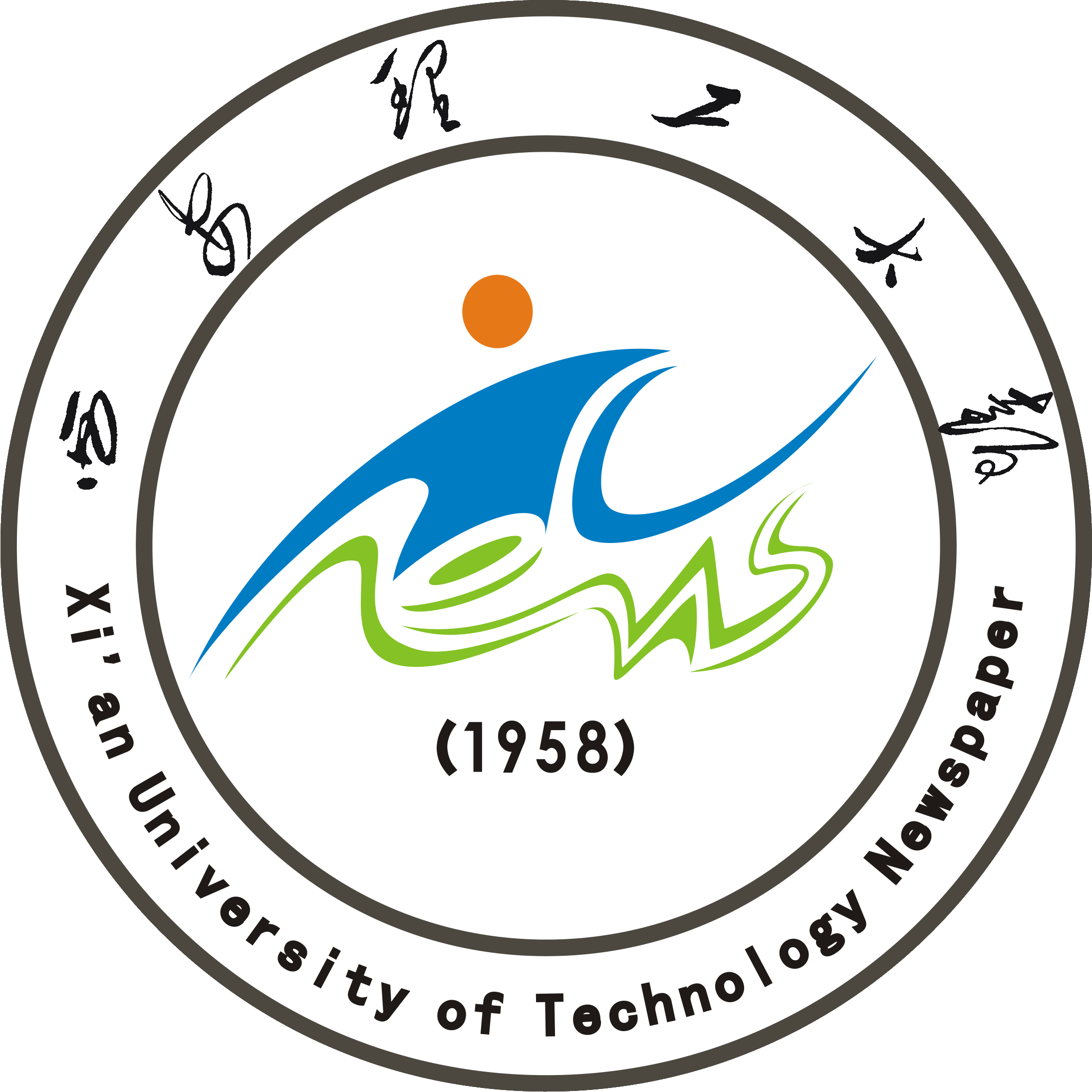很久之前的小时候,听说国外某个很热的国家经历了一个比往常还要炎热的夏天,街上便有行人被热死了。我试想过热死之人临亡之际是何种场景,总不至于忽地融化掉,大概是嘴唇发白,头顶冒汗,晕厥而死罢了。这倒没什么所谓,只是那时想到一个问题:假使让你死,热死或冷死,更好些?答案自然是两者都不好,但这就像A和B二选一,耍小聪明用创造性的C来敷衍自己,问题本身从未直面。于是,此问伴随我好几年,偶尔跳出来打扰一下安静,而试解的答案无论如何也不甚满意。
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往往有春如何,夏如何,秋又如何,乃至冬如何之论。常人眼里,四季如春,四季分明皆是极好,但在我眼里,却是春夏一季,秋冬又一季,甚至简分夏冬两季,春为弱夏秋为弱冬,冬冷而夏热。我是一名地道的北方孩子,家住黄土高坡,虽不是仅余一抔黄土可供把玩,但也打小憧憬旁人所说的南方美不胜收的四季春景,故而曾想,热死倒也不错,只是莫在北方须得在南方啊。
就这般想着想着,几年过去一路走来,我从家乡到了西安。西安夏天热得紧,今年最热的几天新闻上讲有些地方气温高达五十度,幸好没有热死人的惨剧发生,又想过去能将人热死必是没有空调的罢。北方的西安夏天能这么热,已经令我深感讶异,而后来发现西安居然没有冬天,更是着实颠覆了我的官感。每当夏天已过,几场秋雨携着寒意降临,西安便开始了绵长的秋季,在我的家乡已经冷杀行人,街上路人骤少的冬天,西安竟只是还自顾地飘零旧时得意的树叶,让我这个玩笑式自称来自“陕北省”的孩子顿感到浓得抹不开的秋悲。
回家过年之前,在校园弥留之际,我和一位舍友在餐厅前谈过一场话。我说,现在冬至都已过了,近日却总眼前浮现小学时美术课本上的秋画,思考这个现象,我觉得“冬是更冷的秋”,西安是没有冬天的。我认为什么时候冬天到了呢,就是人们感到脸颊冰冷的时候,冬天的风格外刺寒,但究竟是不是冬天到了,实则是客观而非主观感觉的。我又说,南方也没有冬天,一提起北方的冬天,大家马上想到皑皑的白雪,但冬天有雪,反之有雪便是冬天吗?譬如西安不久前也下了初雪,很多人都很高兴,我印象很深(记得还写了句诗“一连阴郁十数日,卧看窗台衣旧湿。”),但这也不能说明是冬天了,就像我此刻脸感到冷,但西安是没有冬天的......最后,我还是没有说出为什么西安没有冬天,与“冷死或热死”不同的是,这次我没有创造C,而是固执地玩着自以为是的把戏——在自我观点上分析问题,也即是逻辑谬误的反证;同样的还是,耍小聪明没有直面问题。
直到我回到家乡。朋友,不知家乡的怯暖是否让你忘记了这场夏洛克观影前的谈话,但我现在不仅得出了西安为什么没有冬天的答案,也作出了热死或冷死的选择。
回家前两三天,我和妈妈通了一次电话,得知家乡零下十几度,不禁感概西安零下一二度的气候算得上暖和了。今年全国寒潮来袭,回家没两三天便见手机上显示气温低至零下二十多度。家这边早已下过了雪,此时地上没有积雪,但呼啸的西北风吹得脸冷得厉害。一如只有苦过,才知道什么是甘甜的滋味,畏惧寒冷,只是害怕感受生命鲜活时的绝望。
我在温暖如春的像鸟巢的家中蜷缩着,感受丝缕般的困意。我想起天空急掠过像蜻蜓一样冻直了的鸟儿;我想起道路旁黝黑的像雕塑一样僵硬的树木;我想起如冰的夜晚月亮洒下的雪花让我在微风中快乐得颤抖;我想起了新生的婴儿刚来到世界的,二十年前的那一眼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