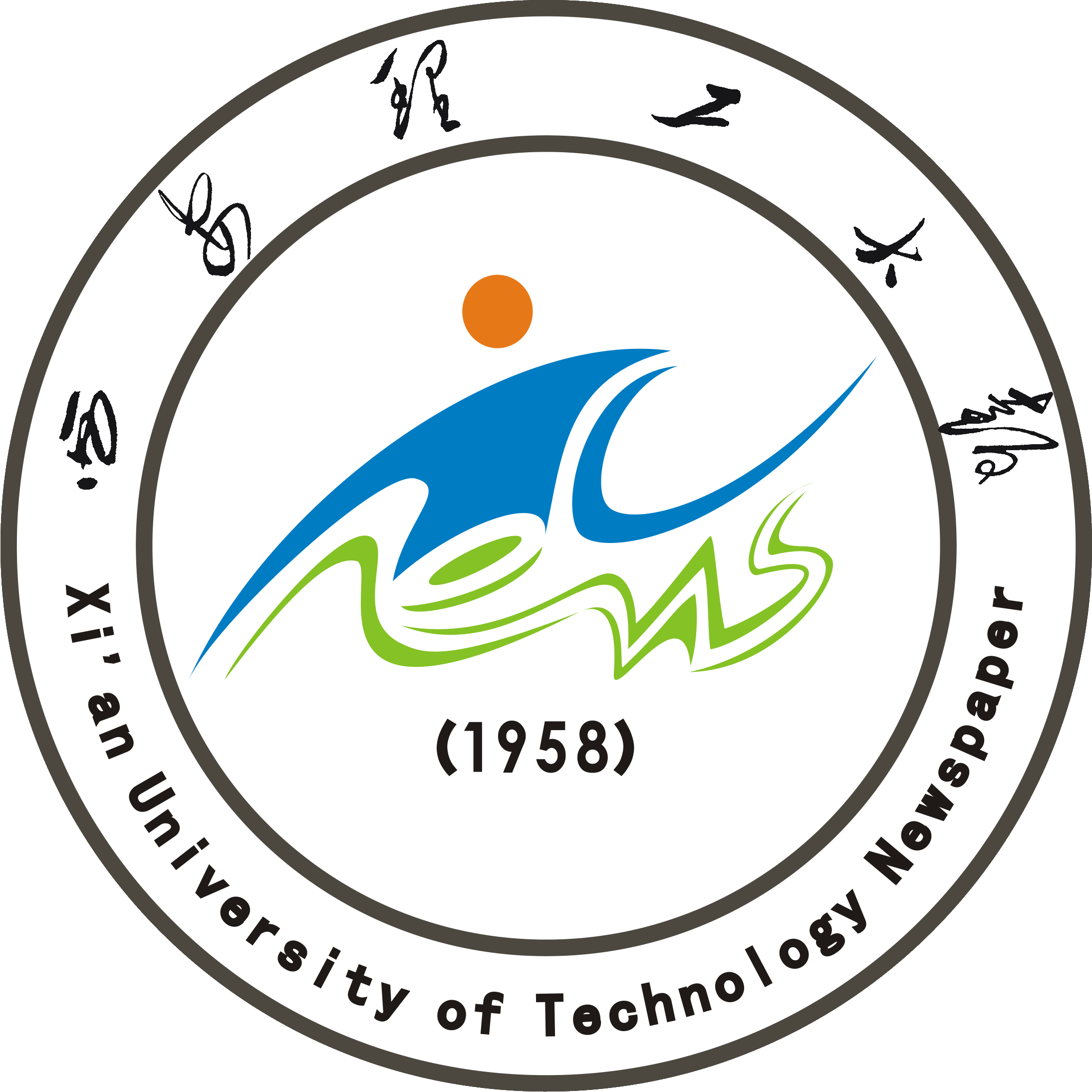天启六年十二月,龙山下了一场雪,晚明人张岱在他的笔记中写道:万山载雪,明月薄之。月不能光,雪皆呆白。斯文者不得不服膺于一个“呆”字,而在有回忆的人看来,寥寥数笔的白描不过戳中乡愁的泪点,落下的不是浮世绘般的繁华素锦,而是昔我往矣的淡淡哀伤。
遥想二十年前,孟庭苇的歌唱得好: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别在异乡哭泣。不知那时她有没有笃信释教。然而,因为此曲,我开始知道世界上有个地方冬天是不下雪的,不下雪,下雨,冷冷清清,仿佛听到了十里之外的雨溅皮鞋声——“扑哧扑哧”。那感觉,一定是浑浊的吧。后来,我在长安街上生活了四五年,每逢春雨沙沙,像蚕食桑叶,楼下的球鞋照例渗过泥水,踩在楼梯上,沉闷喑哑,使人想起: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梦是唯一行李。孟庭苇嗓音纯净,倒是这春天呀,来得太迟了。
是的,长安还是一片雪嘞。黄昏或傍晚,鸟群停落在电线杆上,人一走动便呼啦啦的飞起,像下雨前低飞的蜻蜓一样不安分,那电线杆,被缠裹得严严实实,只掉了几块崩雪。此时街道阒寂,万籁无声,隔着时空,仿佛一说话,声音都会消失。就这样,无声无息中,有个姑娘,陪我走过了整个冬天。有出太阳,积雪消融,哗啦哗啦的流水,地上大块残缺的版图,一点点消失遁形,最后不见,成为路人裤管上的一团泥,一块灰,这比下雨都要难过。
第二年第三年,雪仍在毫无顾忌的下,姑娘人不见了,她的名字大概叫影(隐)。我父亲却来到了长安街上,他给一家公司的老板洗车,寒月里难得一见的硕硕暖阳和煦如东风拂面,我想,是不是该下场雨了。他在玉宇澄清的白茫茫的环境下,工作实不方便,手脚臃肿不灵活,又要钻来钻去,车垢本来就多,油烟熏满了他的军大衣。每次见面的时候,我的神情淡然,轻松自若,转身走了,心里却像压了千斤重鼎,不是滋味。那段岁月,已经忘记了雪是怎样化掉,风是怎样带来花香,只是隐隐绰绰记得闪电般掠过的苍白心情,正如满大街纷纷扬扬正在飘落的雪花。
送走了一年又一年的雪花,我们这帮人啊,多像时间沙漏里挤掉的灰尘。二十三岁,终于知道我无雪可看了,也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世界上有个地方冬天是下雨的。CD里孟庭苇,孟庭苇在唱着:天还是天喔雨还是雨,这城市我不再熟悉。那是不熟悉的一年,压抑绝望,犹如豢养在高高烟囱工厂里的囚徒,希望旋灭,心境晦暗,消消沉沉过了很多个机器隆隆的日夜,仿佛把一生的困厄全都遭遇了。就那样,在年尾的一天,跑去骂了主管辞了职,坐了两天绿皮车,一路找到了会下雪的地方——那姑娘不见的地方,我父亲洗车的地方,回忆温暖并不明亮的地方,我爱的地方。旧历新年的前几天,我爬上了高高的屋脊,夕阳的余晖映衬在我的脸上,此刻万千感慨因心而起,明媚着。冥冥之中,我好像看到了无数的雪花在空中轻舞、飞扬,只不过是殷红的颜色。
是的,毕竟,毕竟长安还是一片雪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