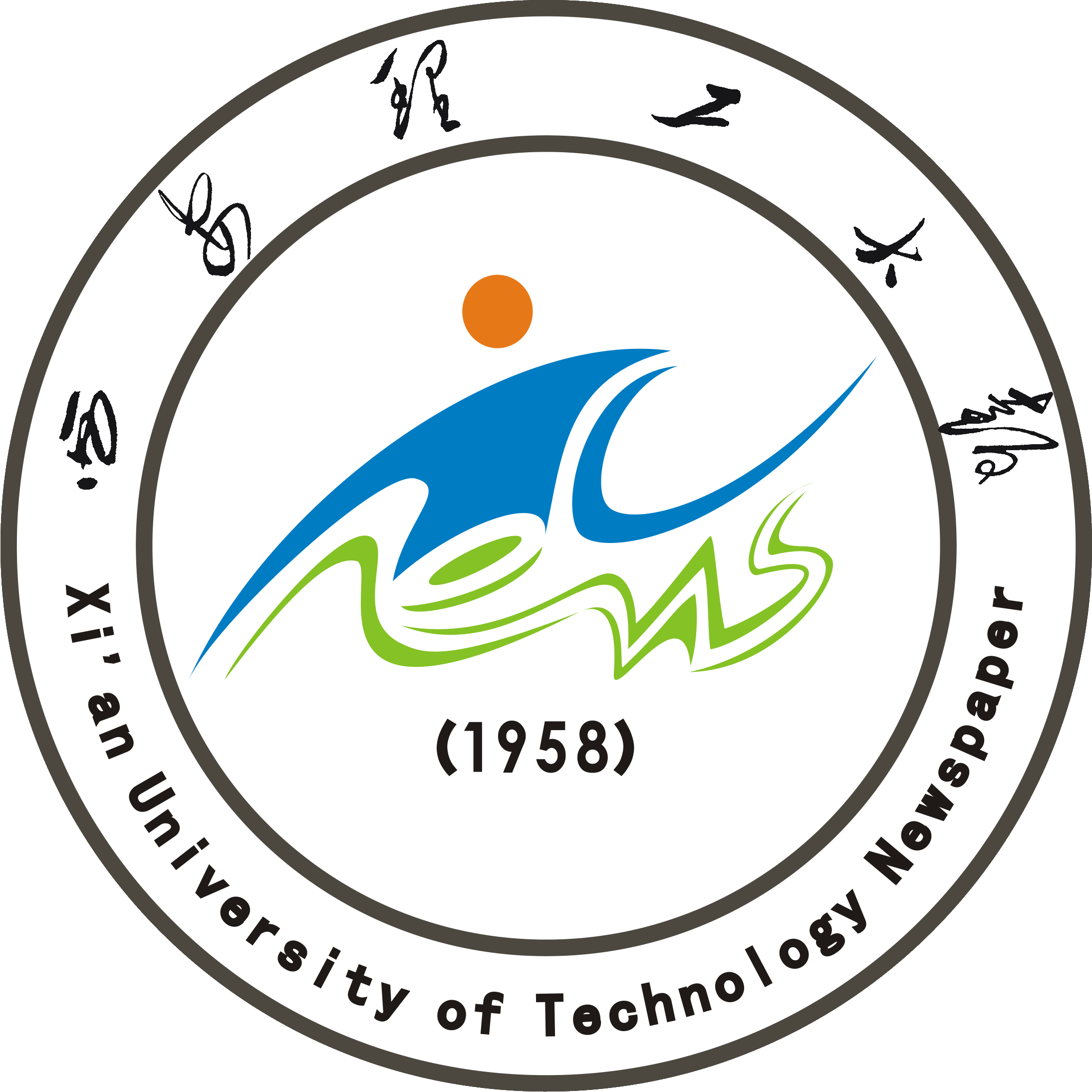前天下午我闯进一条新修的公路,之前有几次坐大巴车经过这里,可是从没有机会在这儿停下来。
一个盘山的大弯道过后,公路的一边变成了一片大草场。现在是春天,草场里开着一道黄一道绿的油菜花。风在吹,花在动,似浪一样的被风儿一波一波地朝前涌,在车上看时,就像万人头顶着一面油彩旗在编排开场舞,和着东南风翩跹,比西北风里的腰鼓舞少一分冲劲,多一分酣畅。情之所起,一往而深。旁边的山峦也蠢蠢欲动,山腰上的连翘叫嚣着,显然底下的万千“士卒”已四面楚歌。
这儿的情景在记忆里变得愈加模糊,像一个焦距被渐渐拉大的长镜头,最后的最后,画面里剩下了一颗孤单的黄色的点,被黑暗绻走,没有留恋的痕迹。现在回头看,故事的发展似乎缺少情节,暴风一样袭来的出场却行走了一条没有头尾的线索,并不紧凑的剧情像杂志里的一首漫谈的诗歌。所以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在恍惚里抓蚊子,春天的蚊子没有叫声,醒来腿脚上被叮了四五个包,不痒却很疼。
我是个总被计划打乱的人,本来这会我应该在啃一根透明的胡萝卜,但是现在我在切柠檬,因为蚊子叮在腿脚上的包很疼,得在上面涂些柠檬水才行。所以啃胡萝卜这件事就只能推到后天下午了,其实我的书签上已经写满了后天下午的计划。正面是给外婆寄一颗高分子聚合而成的树脂牙。这颗牙是我在学校实验室里的一个扣子坏了的塑料砝码盒里找着的,所以我想应该是教授丢掉不用的,可惜他又丢错了地方。他经常犯这样的错,譬如他经常在课堂上把白色的粉笔丢在彩色粉笔盒里,或者把彩色粉笔丢在我的头上,然后落在我新买的白衬衫上。说实话,我一点都不介意,一是因为他已经快七十岁了,我对老年人向来友善,二是因为我有很多白衬衫,都是妈妈买的,她总是说女孩子就应该穿白衬衫,她不喜欢我买的那些大领T恤。我记得柜子里还有三件没穿过的白衬衫,有一件是我特意留下来在毕业晚会上穿的,它是一件束腰的有着蓬蓬袖的白衬衫,我想在大学毕业的时候穿的像一个即将要小学毕业的小公主。书签正面还写了换洗床单,买小西红柿吃和给隔壁寝室的姑娘送一袋小鱼干,因为她养的小仓鼠上星期又怀孕了。
翻过书签我才发现,后面还写着三件事,并且标注了“必须搞定”。其实也不是什么要紧事,就是些被我一拖再拖的“小事”。第一项被重重地标记出来,是向我唯一的室友姑娘讨她这三个月来欠我的债,一共是236块,索要理由是我看上了一条可以搭配我的公主衬衫穿的红裙子,这个理由我想她会接受的,因为她是学芭蕾的,抵制不了裙装诱惑,包括对她身边的女孩,她也希望她们可以像她一样衣柜里只允许有一条运动裤存在。第二件“小事”是抓一只蝴蝶做标本。这件事是我上大学之前答应那时在上四年级的小表妹要送她的小学毕业礼物,可是我在大学里一直没找到抓蝴蝶的地儿,学校的花圃里种的都是月季花,可是蝴蝶喜欢野花,尤其是那种黑黄相间的大蝴蝶,叫什么“黄菠萝凤蝶”还是“柑橘凤蝶”的,它们最爱紫色的野菊花。想起小表妹毕业时竟也没想起来问我要蝴蝶标本,不过她向我讨要了一本金装的《奥德赛》,我忍痛割爱。她现在都上初中了,我寒假回家时,她在做自己的成长记录本,突然就想起了这回事,我当即答应她这个春天一定逮到一只黄菠萝凤蝶做标本送给她。最后一件“小事”还真是“小”,就是一定要把寝室里那只叮了我的蚊子从阳台的窗户里放出去,我可不杀生的,芭蕾舞姑娘也是个从善的人,可是我想这件“小事”并不好办。
涂完柠檬水,我走到阳台,太阳正赶着下山,地表的热风被送到阳台,吹得我暖暖的。想着后天下午这会儿我应该已经放走了那只蚊子,不,或许要再晚一些。赶走那只蚊子后,我就对着远处那些坏掉的路灯吹口琴,曲子是新学的,叫《乌兰巴托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