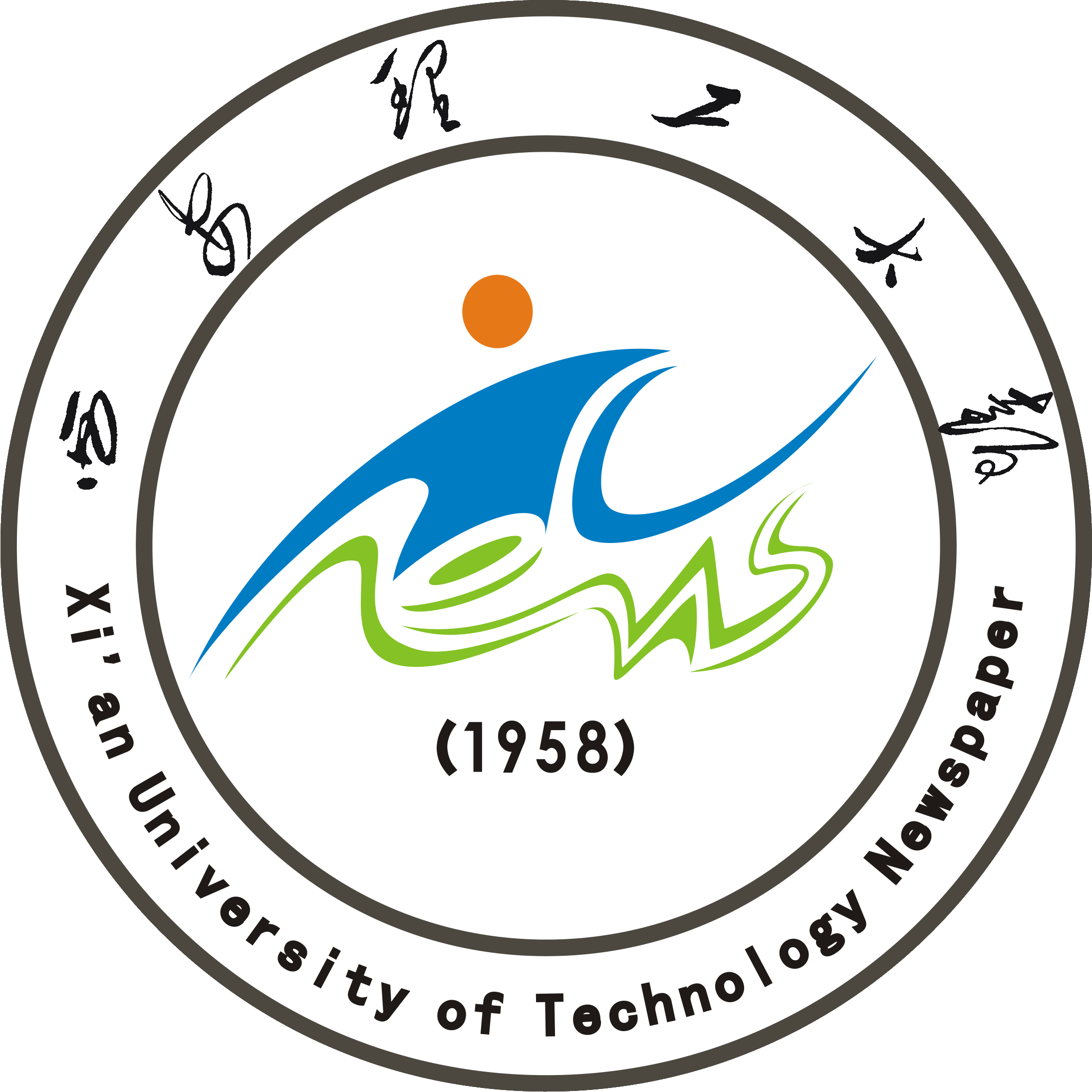十八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瞪着一辆破旧的大金鹿牌自行车,鬼一般穿行在白杨林里。知了们看我抖动的车把左右摇晃,呼叫得更欢快,歇斯底里地呐喊,无名飞虫扑闪双翼划过我朦胧的双眼。这种笨重的大金鹿车驰骋有力,虽无山地车的轻便迅捷。我无畏地在白杨里横冲直撞、左右摇摆,前进又折回,我想我以后怒放的生命,也要如驾驭大金鹿般左右逢源,坦荡无垠,即使大路朝天的偶然间,荆棘和沙尘纷至沓来,我会冲破该死的阻挡。
我记得在高大、高大的白杨树林里,奶奶曾给我讲过纺织娘的故事。纺织娘不是纺织的娘娘,娘娘娇贵着呢,怎能跨上纺车,奏出花木兰姑娘都充耳不闻的机杼声?纺织娘不是村头纺棉的大娘——那挑灯夜作、为游子纺织棉衣的慈母呵。其实,在亲爱的奶奶的眼里,纺织娘就是一种丑陋的甲虫,类似于天牛、金龟子之类,只因扑闪翅膀嗡嗡作响,宛如纺车的奏鸣。因此,奶奶给予这些生灵们一个温馨的名字——纺织娘。这种可恶的甲虫常被我们这些孩子拿来玩弄:剥离高粱茎的硬质外皮削尖成针状,插入甲虫的屁股内(谁知道它们有没有屁股),这些玩意儿依旧顽强地闪着翅膀,费尽力气地挣脱我们,左倾右倒地逃离。它们的平衡已然被顽劣的孩童破坏,身体也被孩童弄残,它们终究飞向何处?生命是否即将终结?在痛苦地从低空飞向蓝天时,它们是否诅咒这些荼毒生灵的孩童?
奶奶眼中的“纺织娘”
其实,纺织娘是真实存在的一种昆虫,学名叫做螽斯。《诗经》里早就有生动地描述:“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的叫声具有金属的感觉,比蟋蟀的更响亮、尖锐而更加刺耳。螽斯的个头与鸣声也不尽相同,体型亦有差异,有瘦长的纺织娘,也有短胖的蝈蝈。蝈蝈,这种玩意儿,老家十多年前异常多的,俯拾即是,俗称“油的”。我当小孩那会儿,也时常把玩。纺织娘我也见过。只是现今,农药的淫威之下,难以寻觅曾经遍布农田的蝈蝈和纺织娘了,就连青蛙也躲着人们的世界,何以聆听那清脆、响亮的蝈蝈的奏鸣。
奶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知道纺织娘引申出如此多的含义。这当然有奶奶的局限性。就连我这个自以为是对自然科学兴趣单薄的混沌青年,如不是对“百度搜索引擎”的熟练运用、对过往美好的热切关注,也不会写出上面一段文字。现在的很多年轻人老纠结于“房事”(房子的事)而削尖脑袋的,少有心思去学习和补充一点点自然学、社会学知识,增长些许的见识尤其难能可贵。正如我一如既往地批评之自我批评一样,我感觉万分的悲哀。我时常嘲笑我自己的无知、懦弱、庸俗。我常常感觉我连沧海一粟都不值,孱弱地如茅坑里污浊不堪的蝇蛆,在做拼命地蠕动、挣扎、生长、成蛹、蜕变,直到某一天化蝶,却变成一只渺小的苍蝇。
于是,我去感受生活的美好,尤其想起奶奶唱给儿辈们、孙辈们、重孙辈们的儿歌时,兴致盎然。
石头裂裂
里边走出个爹爹
爹爹出来买菜
里边出来个奶奶
奶奶出来烧香
里边走出个新娘
新娘出来磕头
里边走出个孙猴
孙猴出来打提(di)溜 ①
…………
① 打提溜,鲁西南方言,荡秋千的意思。
朴实无华的儿歌,看似毫无逻辑、并无含义的说道,其实却在表达着最朴素的一个道理:生命美好,每个人都有自己承担的任务,该干啥干啥去。奶奶一边拍打着我的后背,一边低声吟唱,我做小孩那会儿,常在这神秘的吟唱中进入美好的梦乡去了。奶奶和声细语的吟唱在我的梦里回荡,我的感觉似乎有些变化,那种宛如咒语般纺织娘似的鸣叫,清脆响亮连绵不绝的,在我的梦里激起一阵涟漪似的温热,清晰地传递出普世价值观,在儿歌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得到了最朴素的启蒙教育。
在浩瀚的儿歌文化中,有温婉的批判,比如《小麻雀》:
小麻雀/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烙白饼/卷砂糖/媳妇媳妇你先尝/我到家后望/爹娘、爹娘来了莫让尝/莫让尝……
当然少不了对爱情美好的憧憬,看这首《小红孩》:
小红孩,骑红马,一气跑到丈人家。大舅子扯,二舅子拉,拉拉扯扯进了家;先吸烟,后喝茶,一家人口都见啦,就是没见俺家的她。风吹楼门看见啦,瓜子脸,青头发,上穿绫罗下穿纱。回到家中对娘说,八月中秋去娶她。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三言两语,已有文学意境的清新模样,它勾画出温馨画面,传递着朴素道理。其实,我们常批判农村教育落后,但就儿歌的意蕴看来,农村老太太的教育是最真切、有效的,胜过一切的文字说教。我们无不躺在奶奶的怀里,仰望着星空的间歇间,数不出星星几颗的时候,却在儿歌的潜移默化中得到启蒙教育,甚至我想我最初的文学萌芽就是奶奶亲口传授的。
今天我能坐这敲打着文字,奶奶功不可没。
当儿歌从口中悄然溜走的时候,纺织娘也突然脱离了我的视线,“大金鹿牌”自行车也腐朽地横尸院子角落,一层厚重的灰尘遮住了它的身躯。我早已不忍卒视。谁知道这破旧的自行车曾经承载了我年少的梦想。我当年骑着它在白杨林里疯狂地穿梭时刻,确实幸福得要死了。但老爹这个年龄却不知骑自行车啥滋味。话说老爹上高中那会儿,家里极其穷困,40多里的土路,老爹每周都要往返于学校与村子之间。他背着干粮,踏着“千层底”布鞋,疲惫地望着前方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恢复高考的呼声却此起彼伏。在荒废的土地上渴望种出粮食的时代里,1977年春天,老爹参加了高考,名落孙山,无钱复读,回家种田。从此老牛耕地,面朝黄土背冲天。第二年,老爹当兵去了。不久,身体某项指标不合理,回来了。继续耕种。接着第二年,越南自卫反击战爆发。他所在部队参战,老爹有幸躲过战争。我今天常常不无玩笑地说道老爹,你就是一个逃兵。部队多好的革命阵地,若留在部队也不止于此。老爹羞涩地望着我:你不要步我后尘,不好好工作。胡乱跳槽,你也是逃兵。连个媳妇都找不到。
是吗,我是不是逃兵呢?
我只是不耽于东奔西跑的,不屑于在安逸的环境里乐不思蜀的,只是在匆忙中没有多看她一眼。终究有一天,我也会变成一只纺织娘,冲着那个属于我的方向飞翔。这一天很快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