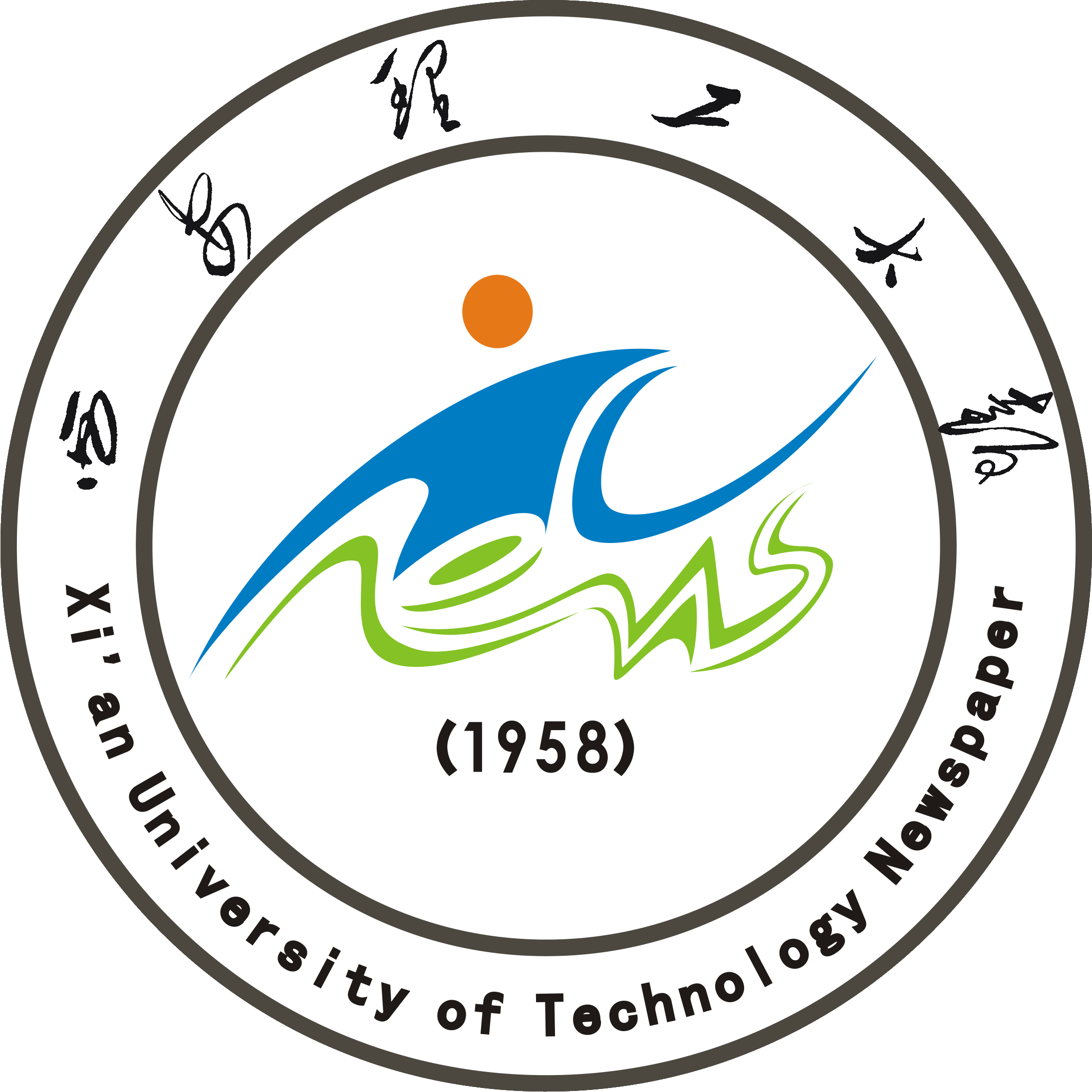小时候,我踮脚拽着你的衣角,你领着我,走我懵懂无知的年少;而如今,我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你的身子,我拥着你,伴你行止艰难的迟暮。
小时候父母很忙,我是寄居在外祖父家里长大的,外祖父是个音乐老师,风趣幽默,见解独特,十分健谈。他喜欢三国水浒,也喜欢战争历史的评议,看书的时候,他戴着老花镜,一手拿着放大镜,这时候,天大的事,他也是不会搭理人的。闲暇的时候也练毛笔字,他的行书很是流畅,就算外行也觉得赏心悦目,春节的时候,别人请他写对联,他也不谦虚,铺好纸墨,一挥而就,晾干后嘱咐我一家一家送去,还在背面写上是贴在厨房或是卧室的,十分周到体贴。他吹长笛的时候总是有一种儒雅斯文的书卷气。
外祖父对象棋极为痴狂,一刻也不能忘记。我幼时最爱看祖父下棋,他喜欢用马深入敌后,常常将它摆在钓鱼马的位置,通常只在开盘时用炮,后来就是车一路披靡,记忆中未曾见他输过。他挑选样式简单颜色单一的家具,回来后亲自用毛笔作画,到现在他的衣柜上仍画着鸡犬相争的图,斗败的公鸡的羽毛落在地上,却仍是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傲人姿态,客人来了都觉得生动有趣,只有自家人觉得亲切,又想起家中两个小弟打架的场面,外祖父当年兴之所至,作了此图。他不只为家具作画,他也动手做家具,他用线尺把椅子的面做成弧形,在椅背上雕出镂空的双鱼,用他的巧手装点生活。
有一次外公讲他年轻的经历,讲他得肺结核时医生都下了病危通知书,贫穷的生活让他不得不离开医院,想起家中妻儿父母,便坚持中医治疗,他自己配药,最终战胜了死神。他又讲民办教师出身的他在学校何等艰难,年轻气盛的他跟校长争论,结果几次外调,可是后来全校只有他一个人通过了转正考试,讲起备战的日子,他仍然神采飞扬,丝毫不见倦容。人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外祖父不是好汉,他是千万庸人中的一个,即使时隔多年,他仍为他的少年意气由衷骄傲。他打开他的木匣子,里面有他各种荣誉证书,也有他剪纸的凤凰,他画的双头像,这种奇特的画法,从上看是一名警察,从下看又是一个艳女。还有他的老友的信件,远行的车票和泛黄的照片。或者,这是一个世界。
七月的时候,外祖父精神很好,他执意想去爬山,家里人觉得年纪大了外出不便,可是盛夏难熬,何况他很少如此兴致勃勃,实在不忍心让他失望。我便陪他去天台山。一路风景很好,坐在车上远远的看着云海,放佛置身古画之中,若非山上道观人头攒动,倒真有几分避世得趣味。下车后,我本打算与祖父一同去乘缆车,谁知他竟不愿。他坚持说是来爬山的,为什么一定要坐那铁盒子,好像古代枭首的囚笼。许久未听他如此趣谈,我竟又一次的妥协。天台的山道并不十分险,山梯两旁有扶手,只是光鲜的衣着令游客们无法触碰这满诟的扶手,他们都一路拍照,一路留名,把矿泉水的瓶子错落有致的留在这山中,挥一挥衣袖,潇洒而走。外祖父不愿我扶他,他右手杵着拐杖,左手随着换步的节奏一下一下握着扶手,落满灰的扶手上只有他宽大的手掌印,我走在他的身后,听他渐渐急促的喘息,我却仿佛将要窒息。他开始走走停停,所有的游客中,他最是突兀,头发花白,身子高大,他不像其他人四处张望,他只是停下来抬头看看山顶的方向,仿佛已有极大的动力,又一步一步向前走。他停下来的次数越来越多,半个小时之久我们并未移动多少距离。就在我心里开始盘算怎么说服他现在返回去乘缆车的时候,他突然坐在山道上,大力地摔了拐杖,可是他摔出的拐杖就在几步之遥的位置,想起他摔它时抡圆的动作,不免有些心酸。我上前去捡他,他连着喊“不要它”,他低着头,似乎已不愿多说什么。我看着这个虚弱的老人,他也曾被上帝垂青,他也有绚烂的青春,健康的体魄。他一路走来,不曾被疾病打垮,不曾屈服于贫穷,他曾在战乱中挣扎求生,在饥荒的年代倔强高歌……而这些,都已成为过去,此刻的他,已是风烛残年,他要每天三次的服药,三高的体质令家人时时担心,他有时候甚至不记得到底服没服过药,不记得随手放下的东西,他要靠着拐杖才能行走,凭借每天的牵引训练才能减缓颈椎疼痛,晚上他要喝一点酒,这样睡着才不会醒来太早……我们早早下了山,从此再也没有提过爬山的事,仿佛我们的记忆在此断片,想起他像孩子一样仍拐杖的时候,想笑又想哭,一股酸涩与无力涌上心头。
时光让我们角色互转,老人年岁渐大,返璞归真,有了孩子一样的固执坚持,而我们逐渐成长,面容稚气将脱。我们都是彼此的孩子,在有限的时光无限温存,真诚祈祷,愿免你疼痛,赐你安好,健康安宁,平安和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