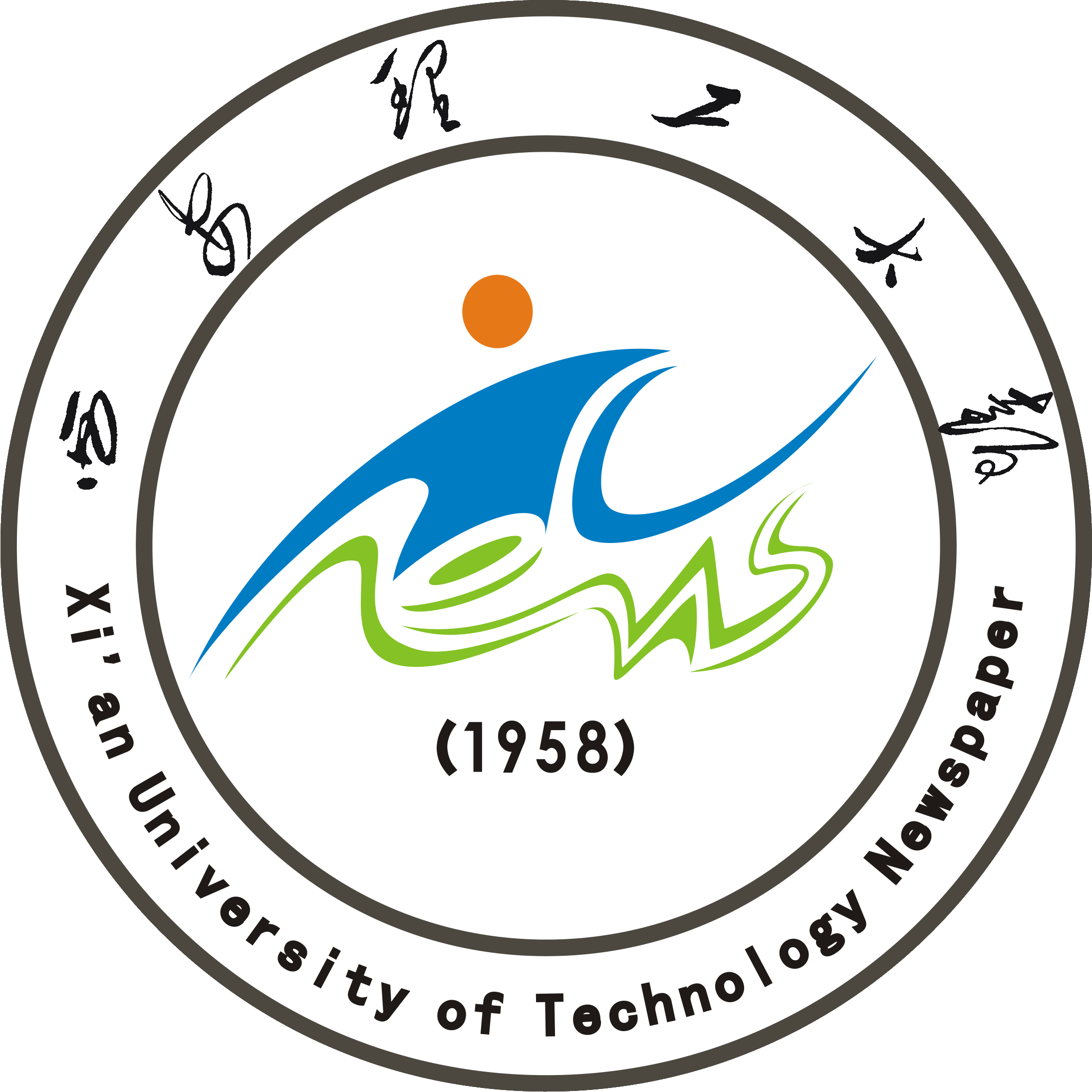河山观是学校为数不多的一座凉亭,这名字既俗且雅,也不知道是谁起的,为什么而起的。总之,我来的时候它就在那里,我走的时候它还在那里。那里的藤萝并不为我的到来增减一份,倒是在我心里,我心里已经嗒然若失。
那是六月最昏暗的一天了,雨疏风骤,我在最高的楼台眺望,墨色泼在了迷迷蒙蒙的大地上,重处如湿宣纸,慢慢浸透其中,轻处如涂蜡膏,晕出粗笔轮廓。这片雾气胀着,浮着,树叶随它飘动,枯槁,光线随它舞蹈,幻灭。看见伞了,花花绿绿的伞,倾斜的伞,摇下雨滴的伞,遮住人脸的伞,凡此种种,就像日本的浮世绘,拽着一缕风情招摇而过。
我想,我与他们不同,在雨中我不用撑伞,可以一径走到凉亭,凉亭下的蚁穴集了又塌了,去年的两朵午荷聚了又散了。
幸好还有这一朵留着慰藉心意。
白色娉婷,四个瓣舒着,托起了一方矮矮的天空,如同坐井观天的人看到的天,荷叶也在看着她的天,尽管低垂,渺小,也许一个星夜只能看到一粒星子,这片天空还是经历了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一朵午荷,只不过是几个月匆匆的光景,在这光景里,她与青蛙窃语,与水虫和音,与岸上的松树同享雨露阳光,同样,她也经历怅惘,当秋风减紧,霜冷关河,木叶纷纷而凌乱,昆虫嘶鸣而沙哑,当星气微茫,银河回荡,落花龃龉而悲伤,翔鸟踟蹰而忧悒,她以枯萎的容颜面对山河景象:河山观,河山观,河山不复,何来观?
我坐在绛红色的长木椅上,藤蔓悠悠的窜下来绕住我的项子,湖水也以绿的发腻的镜子倒映着我的粗糙容发,我的指甲抵进泥土,不曾带走这里的每一寸土,我坐在绛红色的长木椅上回想着我的往事,我的爱情和我的梦想,这是唯一不让人自惭形秽的地方,也是唯一颠覆了又重新唤醒回忆的地方,我想象这里的鸟儿和我相熟了,每天清晨都啁啾曲儿给我听,这里的青草又湿又滑,鞋底上沾满了它的唇印,这里的月亮又圆又大,几百个屈原,几百个苏东坡也吟哦不尽,这里的七月像啄伤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雄鹰,也啄伤了我。
一朵午荷,她在微风中扶着腰姿,她颔首搔头,她在等木匣子里的玉簪子,她为去年失去的另一朵而兀自伤怀,她临水照影,对月嗟呀。一朵午荷,她呢喃着姹紫嫣红开遍,悲惋着易得凋零,无情风雨,惆怅着终归净土,雪落满山。一朵午荷,在红尘中渡过莲子,渡过看花人,渡过青灯照壁,冷雨敲窗,渡过暗自思量的无眠影。一朵午荷,在佛祖的脚印下,穿越过千年的禅语,皈依过古昧的禅火,在烛照香熏之中,咧着嘴笑着:开出一贯莲子。
我再也回不去了,一朵午荷,她已凋亡,花瓣儿纷纷落了,落了。明年的看花人,劳你亲手相存,落掉的花瓣,是一份没有字的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