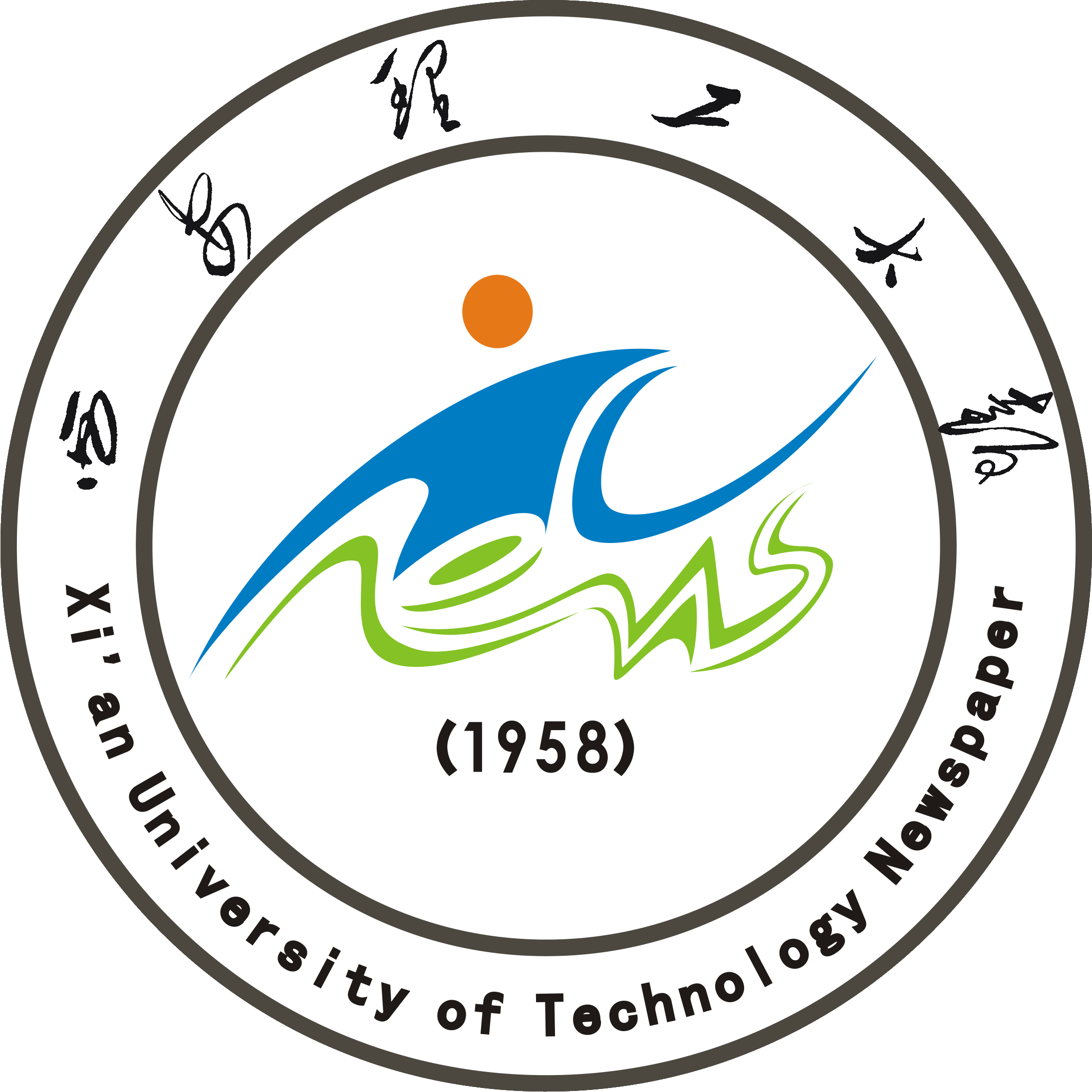最怕西安的夏天,挂在当空的毒日头如同火炉一般整日家炙烤着的大地,每个旮旯里都是翻滚着的热浪。在这热气袭人的季节,人也容易变得烦躁。有的时候着实想找一块清静的地方,却实实的难觅,俗话说“心静自然凉”,我愣是静不下来。现在虽然比较忙,但时间倒也自由,有的时候也就给自己找个理由放一半天假,整天家衣衫褴褛的躺在凉席上,床头放上一杯凉茶,手中捧上一本沈三白的《浮生六记》,看那沧浪亭泮伉俪纳凉逗趣、携手望月的情景倒也让人觉得舒坦。今天晚上气温突然变得温和起来,外面飘荡着少有的清凉,我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悸动,跑出宿舍楼去外面兜兜风。
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忽然想起前两天我一个同学从家归来说他们家正在收麦子。“哦,现在已经开始收麦子了”,我当时似恍然梦醒般重复了一句,接着又说“我家乡现在还不到时间呢,每年小暑前后才是收麦子的时候。”好几年了,不曾看到家乡收麦子的情形。那情那景,全是儿时的记忆。想起小的时候,着实让人怀念,收割麦子的季节全是大人们的事,我们小孩子便如同脱缰的野马漫天世界瞎转悠。最忘怀不了的便是那宁湾梁上的一排排偌大的白杨树。等忙完夏收,大家也就消停了下来。吃过午饭,男女老少也都不在家呆着,都跑到那白杨树下纳凉。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的抱膝而坐,有的盘腿而坐,有的半卧着,有的平躺着,小孩子们则在大人们中间乱窜,你追我赶,好不热闹。有的被追的太急便一头扎进爷爷奶奶的怀里,差不离就把老爷子撞了个人仰马翻,老爷子佯装嗔怒的举起巴掌一边往孙子的屁股上按,一边还说“这小杂种,我煽烂你的屁股,叫你不安生。”旁边的叔叔婶婶们就戏谑着说“你爷爷给你捞痒痒呢!”逗的大家一阵哄笑……
现在每到夏天,我总是想起家乡:那片天,真蓝;那缕风,真凉;那延绵不绝、逶迤起伏的山,真翠;那跌宕潺湲、舒缓有致的水,真清。尤其躺在那白杨树下,近处树叶沙沙不绝于耳,远处蝉声聒噪于天,睁眼望天空云卷云舒,闭目听山间如律如音。一不小心就睡着了,毫不察觉又醒来了。等大人们全都去忙夏收了,我便撺掇上一群要好的死党去偷人家的苹果。等到晚上吃过晚饭,被偷了果子的那家媳妇便站在宁湾梁上开始骂村了。那辞藻确实难听,那声音着实动人,悠长、婉转,像一首高亢激昂的音乐,似乎是为炊烟笼罩的村庄在奏起的一首凯歌。
那天一个老乡打电话给我说,马上到端午节了,到时候要过来和我聚聚谝一谝闲传,我心里倍感欢喜。想必大家和我一样,在这样偌大的城市能找一个人和自己用家乡话闲聊的人很是让人欣慰。想到端午节,不禁让我想起了去世已经快三年的奶奶,奶奶去世的时候我不在场,所以到现在还恍恍惚惚觉得她老人家仍在世,只是再也看不到她的音容笑貌了。在我的记忆中,她除了腿脚不便之外,身子骨一直很健朗,七八十岁了,饭量比我还好,尤其她那爽朗的笑声活像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小的时候,每到端午节,奶奶总是起的最早的,等我起床的时候,她已经从外面采摘艾蒿回来了,她把折回来的艾插的到处都是,门楣上,窗台上,灶头上,柜子旁,凡是人经常接触的地方都有,她说艾能辟邪驱虫。每次折艾回来,她两腿总是湿漉漉的,身上也总是飘着艾草的一股清香,我最喜欢那种味道,多少年仍然不能忘怀。突然想起诗经里的两句话“野有蔓草,零露瀼瀼”,用这两句话来形容家乡夏日的早晨再也恰当不过了。
说到家乡的端午节,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就是家乡的草莓。一提起这两个字,涎水便不禁下垂。家乡的草莓,虽是野生野长的,但颇为丰盛,多生长在那些被遗弃的荒地上。草莓的繁殖能力特别强,所以那些荒地几乎全被草莓占领了。家乡的野草莓花瓣多呈白色,花蕊呈柠檬黄,一两株可能不足为奇,但若你见了满山遍野的草莓花,你绝不会因为她的身材矮小,花朵平庸而瞧不上眼,相反,你定会为如此壮观的草莓花而惊喜若狂,着实为一处大观,真可一饱眼福。一场雷雨过后,花瓣便零落的满地都是,残缺不全。枝头上就露出米粒一般大小的果实,一眼望去,密密麻麻的,甚是令人心然怦动。瞅着它,盼着它,颜色由麻黑逐渐变成麻黄再到泛白。果实上的种子像针扎的窟窿一样渐渐变得稀少,从小米粒到小拇指一般大,再到大拇指一般大。等熟透了,整个荒地上就像落了白茫茫一片雪。除了白色,也有不少红色的,零星点缀在白茫茫的草莓中间,煞是可爱动人。到这时,草莓全身的种子也就约略看不见了,只剩下针尖大小的一个个小窝儿,给人一种轻盈空透的感觉。每到端午节,正是家乡摘草莓的盛大节日,早晨媳妇婆子在宁湾梁上你呼我喊,三五成群的挎着篮子浩浩荡荡地就出发了,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诗经》中的“芣苢”篇,把此处的芣苢改为草莓再恰当不过了——“采采草莓,薄言采之。采采草莓,薄言有之。采采草莓,薄言掇之。采采草莓,薄言捋之。采采草莓,薄言袺之。采采草莓,薄言撷之。”清代方玉润对原诗歌评价说: “ 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
小时候奶奶经常带着我去摘草莓,事实上,与其说我是摘草莓,还不如说是吃草莓来的更准确些。即便是吃,我也不好好吃,和其他小孩子在漫山遍野的草莓丛中嬉闹才是我最大的乐趣。结果是,在回家的路上,不停地在奶奶盛满草莓的大篮子里一把一把的抓了草莓往嘴里塞,惹得一起行走的婶婶们都嘲笑我。
去年夏末的时候回了一趟家,院子里的苹果熟的正透,似乎在专门等着我回去摘呢!那是奶奶在我出生的那年种的,和我同岁,现在枝叶繁茂,已经覆盖了几乎半个院子。
今晚,也许是突然降了温的缘由,校园操场上招惹了许多人,熙熙攘攘,或三五成群,或成双成对,在朦胧的夜色下,感受着夏季少有的清凉。我靸着拖鞋,穿着背心和短裤,左手拿着一瓶驱赶蚊蝇的花露水,右手拿着一罐啤酒,捡了一块人迹稀少的地方坐了下来,在身上和周围喷撒了些花露水,然后仰头喝一大口的啤酒,喝完了还砸吧两下嘴巴,别有一番味道。周围的人或窃窃私语,或高谈阔论,独我喜欢望着这深邃的太空发愣,一缕带着少许热气的微风拂过,吹落了我一身的躁动。望望远方那灯红酒绿掩映下的城市,隐藏着多少喧嚣与浮躁,哪里寻得到家乡的半点宁静,何处觅得见家乡的一丝清凉。雾霭沉沉之中,那是家乡的缩影;思绪飘荡之端,那是儿时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