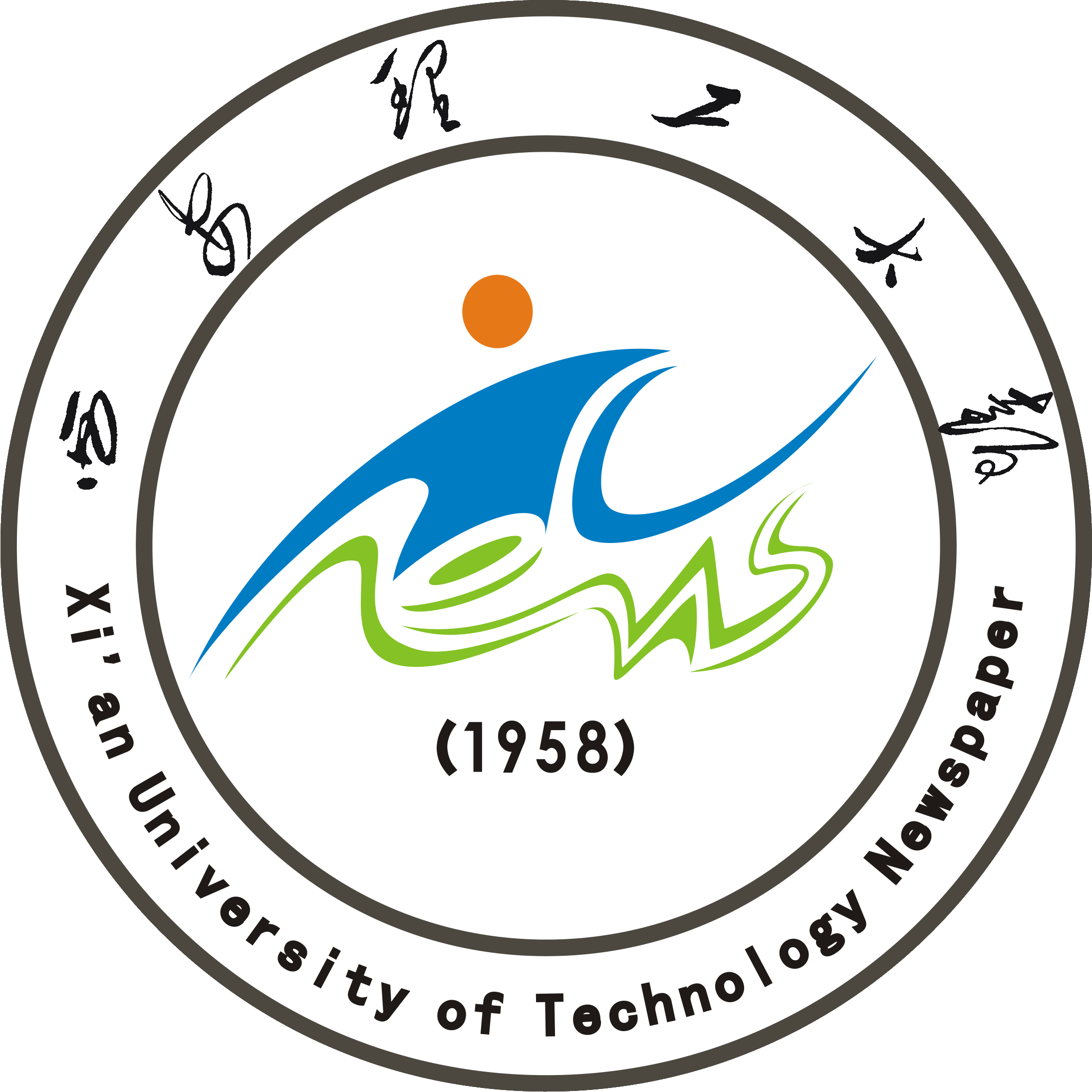昨儿听说内蒙下了场大雪,所以其它地方爱雪的人就只能等雪,盼雪。
年少的时候,对雪的真挚情怀来自《湖心亭看雪》,因为是在一个朔风凛冽,大雪深数尺的日子里背的:“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一边想象自己应是那面对“唯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的“痴相公”。
张岱晚明人,因为《石匮书》未成没有殉节,《陶庵梦忆》写了两次雪,一次湖心亭,一次龙山,湖心亭看雪颇具天人合一的味道,龙山雪则更富有生活气息:“万山载雪,明月薄之,月不能光,雪皆呆白”,“马小卿,潘小妃相抱从百步街旋滚而下,直至山趾,浴雪而立。余坐一小羊头车,拖冰凌而归。”既是回忆性的小品,也不过是“梦醒时含泪的微笑”罢了。
但很多年后,我依旧忘不了张岱,忘不了《湖心亭看雪》,因为他在陶庵下,在西湖畔,扑捉旧事,同样,我也在倒带旧时光,在沉思中追忆那些鲜活的日子,不再复活。
以前的下雪天,不必搭车,不必蹬脚踏车,早上起来喝杯热茶暖暖身子,对着窗子哈几口热气,沿着空旷的街道走,不管有没有麻雀倏忽腾起,雪花溅了一枝,不管有没有车铃叮当,偶尔过个匆匆的小贩,不管有没有烤红薯的清香,热腾腾的豆花脑,不管有没有冷风扑入胸膛,刮得手指头皲裂,只消不出太阳就好,不必打伞,不必带帽,围个大脖子围巾,从早上走过中午,走过人家吃午饭的时间,大风大雪的,心里却无比惬意。那年冬天和W一块走,头顶冒着飕飕的冷气,穿过旧时的铁轨,穿过医院,五金店,穿过广场,挂雪条的电线杆,穿过从车窗内跻出一个脑袋默默吸烟看雪的人,好像把一生的路都走尽了,天气虽不明朗,冰凌容易摔倒人,一想到这里,觉得总是暖的。现在W在南方,南方的雪似乎不如北方的迅猛了。
再二年,冬天过得冷清而寂寞。去街上买个红薯,却食之无甘,好像在嚼一个圆木头。每夜回家的路上静静走着,凄美的月光洒了一地,雪的洁白也显得骚动不安,耳里插着静茹的歌:“一个人静静走在回家路上,而起风的夜晚有一点凉”,心里揣着空空的自由。想去兴庆宫看雪,那边有一个大湖,湖上卧雪的时候,亦是张岱笔下的情形:“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我便亦可以坐在亭子上,随万物静美,大悲大喜尘埃落定,万事万物沉淀为湖上一点冰粒,一片幽寂,什么东西都摒住了呼吸,不再流动。
今年的冬天我想起好多旧时光。捧着几米的漫画,名字格外省人:“童年下雪了”,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这些渗透着凄凉的文字,我想等到下雪天去湖边的小亭子上背,它们作为新时光,未被散落的珍珠既令人歆羡,又在冥冥之中使人觉得兹此注定怀念.我想象不出在古城的湖上,万籁俱寂,只有雪打枝头,压断树枝的嘣嘣声,只有雪敲湖面的清脆声,那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
离开了堆雪人,打雪仗的年代,离开了好朋友,并肩走的年代,重新审视别人的回忆,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不敢看第二遍的《雪国》和《伊豆的舞女》,不敢看第二遍的《古都》,前者充斥着和雪相关的忧伤,后者流淌着暮春樱花纷飞的恣意悲凉,一如《樱花纷飞时》里唱的:“不久后的我们俩 将要去何方 即使 剩我一个人 如今也要 确实 轻轻的拥抱 银装素裹 感情坠落 脚印褪去 声音消失 树木们总是 守护着这思念 停留在‘永远’中的我们俩 在此继续生存。”
写着写着,天放晴了。我期望着“今夜有暴风雪”,即使没有,我心里也住着一座城,名字叫“雪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