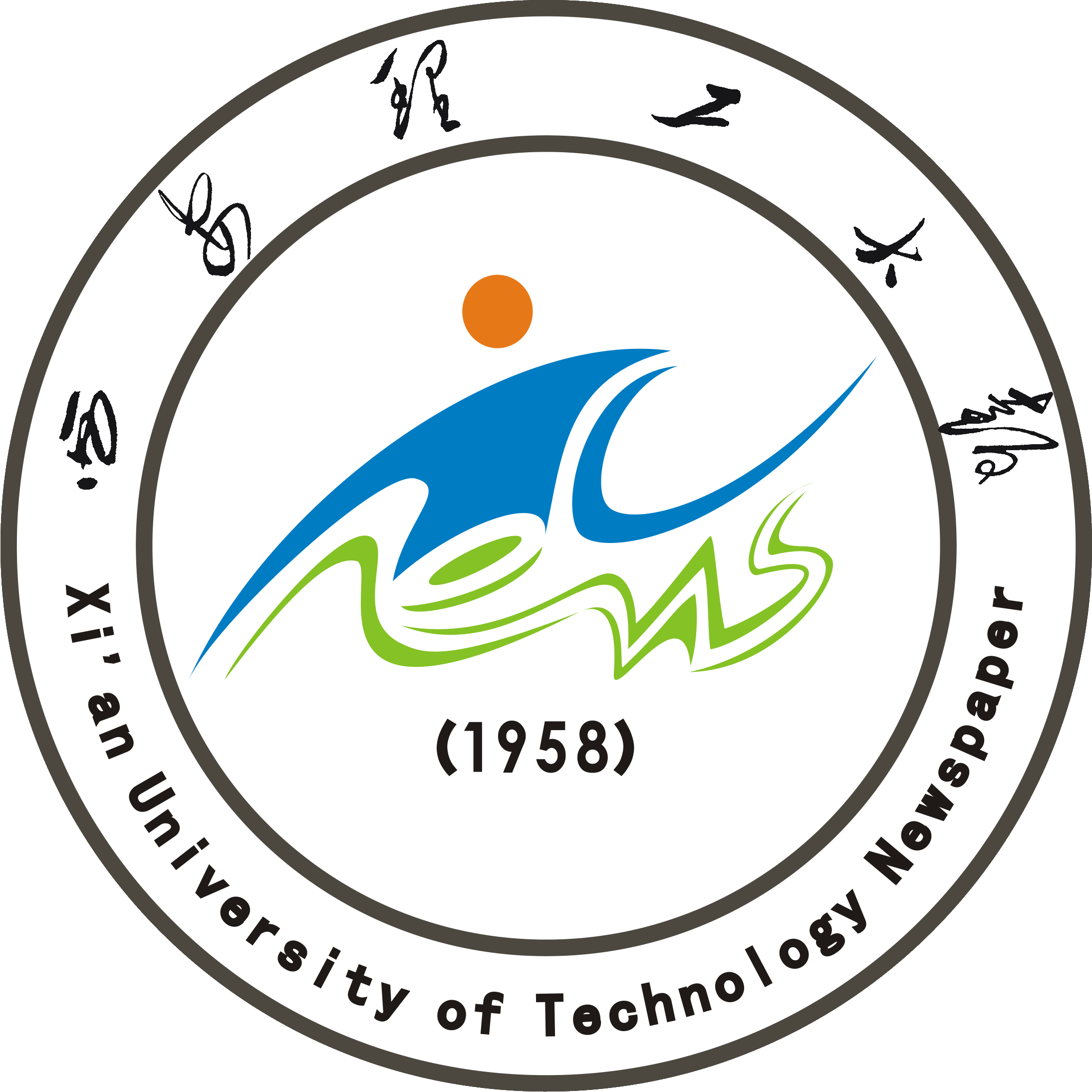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站在高高的田畔上,拔着麦田里的草,一脸沧桑。外婆喊了她一声,又推着我向前去叫她妈,我才猛然意识到她原来就是我妈,可是当看到她满脸沧桑的额头上那硕大的一块伤疤时,我却吓得没头没脑的将脑袋往外婆的怀里钻,说什么也不到她的跟前去。她呢,尴尬地笑着,自嘲地说,儿子,不认识妈了。而我,却将头埋得更深了。
那一年,我9岁。
也就是说,我9岁以前,是没有见过她的,其中个把原因我无从知晓,只是从外婆口中得知,她把我抱回家时,我在这个世界上只生活了3天,眼睛还没睁开呢。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就恨上了她,恨她对我的绝情。甚至在我9年的成长中她看我的几次时,我都躲到别的地方去,我,只是不愿见她。
或许是因为愧疚吧,在我9岁回来之后,她总是想方设法的为我弄好吃的、能补身体的东西,由粗到细,由昂贵到廉价,各种各样的食品她都用尽方法搞到。因为我,家里过年用的红枣早早就泡在了米锅里;因为我,她存了大半辈子的钱很快的瘪下去了。平日生活里,她总是喜欢用粗糙的手掌摸着我的脑袋说:伢子,妈对不住你啊,都这么大了,妈还没有好好地看过你呢,来,让妈好好看看。我却倔强的将头一撇,不让她碰我。我还是恨着她,即使她为我做了这么多,我从没有叫过她,9年的恨,漫长得无边无际,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家门口就是渭河,我常常跑到那河畔上看那流水潺潺淌过,也看着那河水从9年前的微浊变为今天的臭水。在字典上学了泾渭分明的词语,知道那‘渭’指的是渭河,便想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个样子的壮丽,于是便一个人沿着河畔往它的尽头走去,一连几天几夜。也不知道是什么给了小孩子我那时那么大的勇气,我竟在那几天里无从感到害怕。只是当她找到我、她布满泪水的脸贴在我的脸上时,我才觉得恐惧。可我推开了她,一个人回到了家里。
农家的日子是很平淡的,似水流年,又如无风的水面一般,平整如镜。可是季节却不似这农家日子一般平静,十五岁那年,渭河洪水了,家也被涝了,粮食自然也没了,无从投路的我们就只好去临县找寻落脚的地方。一路上,她男人似的用一根扁担挑着从水里救出的些许生活物品,吃力地喘气,却还不住地问空手的我累不累,要不要歇一会儿。我觑了一下她,以示自己很好,却不再多话。我还是恨着她,此恨绵绵无绝期啊!
在临县,我们住了5年。我20岁了,她50岁了;我变得强壮了,她的腰却弯了下去;我走进了大学,她却只能在家里回望我;我满头青丝,她却已有白发印上两鬓…… 学校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眼花缭乱得让我初始竟找不着北,不久之后我就适应了,适应了那奢靡的生活,也在大一下学期结束时成了一个彻底的烟民。
大一的春节我没有回家,同学问我缘由,老师要我理由,我笑笑:没有车费。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单亲的孩子,也没有告诉他们我和自己的母亲之间的矛盾很深很深,以至于我不想回家,只为了不要见她。我对她的恨已经太深了,抹也抹不去,散也散不开。
她知道我不回家的缘由,但她并未说什么,只是托来西安的看亲戚的老乡捎给了我很多的吃食。可到了我的手里时,已经所剩无几。其余的,被那个老乡吞了。我郁闷她笨,邮寄那么发达,能花几个钱啊。我没有告诉她这些,于是她也就觉得我已经收到了,就没再有什么表示。日子也就平淡了下来。
我是在午夜被电话吵醒的,是她。话筒里她抽泣着对我说:伢子,快回来,你奶不行了。我忽然间就感到了寒冷,直接就挂了电话穿了衣服去了车站,火车是不可能坐了,我便找了出租车颠簸的往家驶去。我没有奶奶,我只有一个疼我爱我的外婆,她说的奶奶便是我的外婆。外婆养我长大,在我的生命里弥足珍贵,无论如何我都舍不得她的。外婆,你一定会没事的,一定会的,一定的。一路上我不停的祈祷。
中午的时候我回到了家,见屋里没人,就赶去了医院。当我赶到病房,看到外婆骨瘦如柴的样子时,不禁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跪在外婆的身边,谁都拉不起来,看着她沉睡的样子,我只想好好地陪着她。每听到一次她在睡梦里的呻吟声,我的心就颤抖一次。有人扶着我的肩,轻轻抽泣,我回过头去——是她,我没有反应地转过头来,依然守在外婆的床旁,等她醒来,看看她的孙子。
外婆下午的时候终于醒转了过来,很精神的样子,一点也不同于他们告诉我那样的奄奄一息。我们都很高兴,却不知这是回光返照。外婆看见了我,眼睛亮了一下,招呼我去她的枕边,摸着我的头,微笑着,然后讲了一段令我想死的话。外婆告诉我,她的命很苦,30岁那年生了我,男人就死了,再嫁,男人又死了。别人都说她是克夫的女人,于是她便不敢把我留在她的身边,她怕我也怎么了,她说,要死,就我一个人吧。外婆还告诉我,她额头上的伤疤是我5岁那年发高烧她抱我去医院的时候摔的。那时候村里还没有通公路,她就抱着我跑了几十里山路去了医院。一路上磕磕绊绊,也不知摔了多少次,额头上破了一大块皮,血把包我的褥子都染得通红她都不知道。到了医院才发现自己与我已血迹斑斑。医生一检查,发现她的伤比我的病还要严重,于是便训斥着给她包扎了,我却因为送得及时而没什么大碍。但是她额头上的疤却是一辈子也去不了了。
我静静地听着,发了呆,连外婆的声音低下去都不知道,直到四周的哭声震天喊地的响起来时才猛然回过神来,哭喊她,可外婆却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过了许久,哭声渐渐平息,亲戚们都开始商量起处理后事的事宜。我起身回头,她却不在房间,我走出房外,却见她正伏在椅子上默默的哭着,肩头一耸一耸的。我蹲在她的身旁,扶住了她的肩,喊了声妈,她猛然抬起头,泪光斑驳。我伸手拭去她的泪,又喊了声妈。她忽然间就嚎啕起来,肆无忌惮,令我止住的泪水再次倾然而下。她等这一刻,已有20个年头,20年里,她的亲生儿子,从未喊过她一声妈,她,确实等苦了。
我抚摸着她额头的伤疤,说:妈,我不会让你再苦了,要苦,就我自己苦吧,而不是你。
她依偎在我的身旁,这个死了两个男人的女人,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她额头上的伤疤,在我的眼里,竟然也变得温柔起来。她说自己好久没有这么的快乐了,我亲爹和后爹死后她就没再快乐过。可是,现在她很快乐,很幸福,说着说着,泪水又涟涟起来。
我搂紧了她,心里说,你会快乐、幸福的,因为,有我绵绵无期的爱。
恨了20年,爱终究会来,爱了,也就快乐了。望着远方,我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