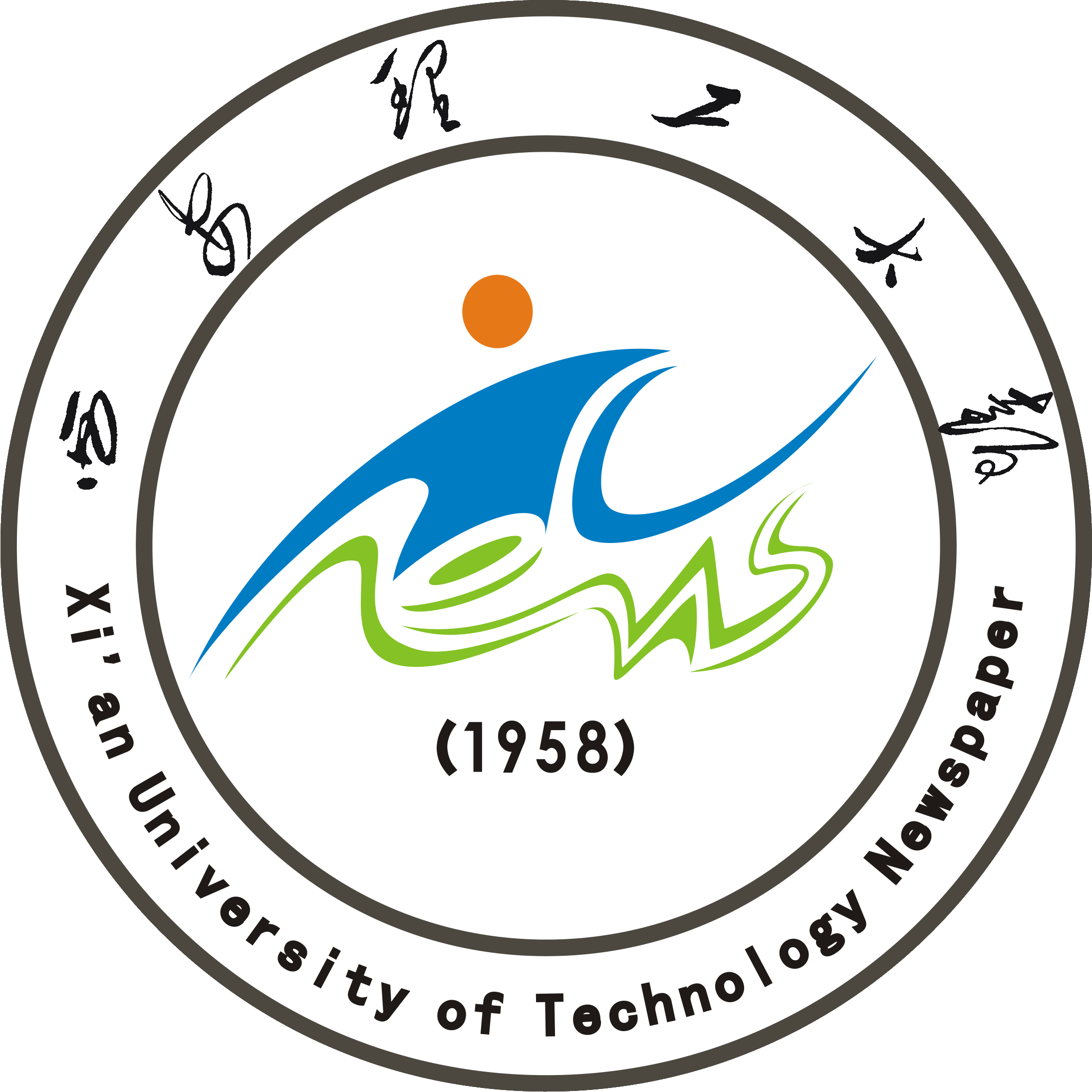故乡麦地的那一畔,有一个祖宗女真将军留下的青冢。
每年冬去春来,麦苗青青,我都会拖着鞋子去那边看落日。
因为冬天还未彻底地溜回去,所以人很少,甚至,一回头看不见另一个人影。
我满怀平静的心绪,斜睇着落日的余晖,像无数条密密的线条,它们投在枯草上,投在落叶上,投在青冢的圆盘上。突然觉得,时间也老了。
时间老了吗?
在我被疑似甲流的那一段日子,也几乎被隔离在方方的墙内,在方方的墙中有一扇窄窄的门,窄窄的门中有一张窄窄的床,我无暇恋及黄昏,看见黄昏我总是恐惧,害怕明天又是重复的一日,打吊瓶,睡觉,出不了门,然后,对着时钟和分钟发呆,心里像一团灰,一涟死水,像被孤烟蔓草重重覆盖,长满了石头。每一次轻易地拨动,是寂寞在无声的歌唱。
终于有一天,我“逃”了出去,知道这样很自私,但还是想看看落日,看看黄昏。
十月的风景令人陌生而感动,高大的桦树林哗哗地被风掠过,我站在泥土上,把手指埋在草丛间,看着落日像没煮熟的蛋心,颜色逐渐加深,变得纤浓,变成绛红,麦地中,只有我一个,一回头看不见另一个人的影子。
很想高呼,却丝毫没有勇气。
一如陈敬容在《山和海》中写得:“高飞,没有翅膀,远航,没有帆。”同样,高呼,也没有勇气。
我把手机关机,不想和外界得到联系。
在这样一个时刻,看看落日,顺便,换换眼界,让该死的时针和分针的交错循环不再浮现在我眼前。
或许夕阳也在看我,或许它也懂得惺惺相惜,像《红楼梦》中说得:“新啼痕间旧啼痕,卿怜我处我怜卿。”它也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我是“心如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两个同命相怜的人,自然懂得相知的意趣。
它越坠越快,绛红色像飞了出来,在霞光万点的那一坨,将它的酡红化作光中飞舞的蝴蝶。
我要去追它,上古的夸父渴死在旸谷,拐杖化作邓林,我没有一种勇气么?
跑着,狂风掠过我干燥的嘴唇,好像跌碎了,再也拾不起来。
跑着,把一切都丢在后方,勇敢地去追逐美丽,哪怕石子磨破我的双脚,在我身后,斑斑血迹,它们会开出一地杜鹃。
跑着,一年后,两年后,又跑回到同一片落日旁,但桦树林已不再。
这是我的家乡,那边的月亮已绰约悬了出来,在祖先的青冢旁,感动和庄严又一次突袭心头。
落日已残,支离破碎的感觉朦朦胧胧地渗透在每一颗圆润的清露上,像笼着一层薄雾。
时间老了吗?人老了吗?
自然和生命的相替总是使人黯然神伤,而身后的麦子却是青青,东风十里,短暂的余晖洒在麦苗上,即使有太多的眷恋,也是被夜的浮沉一笔带过,欣欣向荣与凋落萎靡,正是大自然的秘密。
跑吧。
即使没有留下足迹,我也已经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