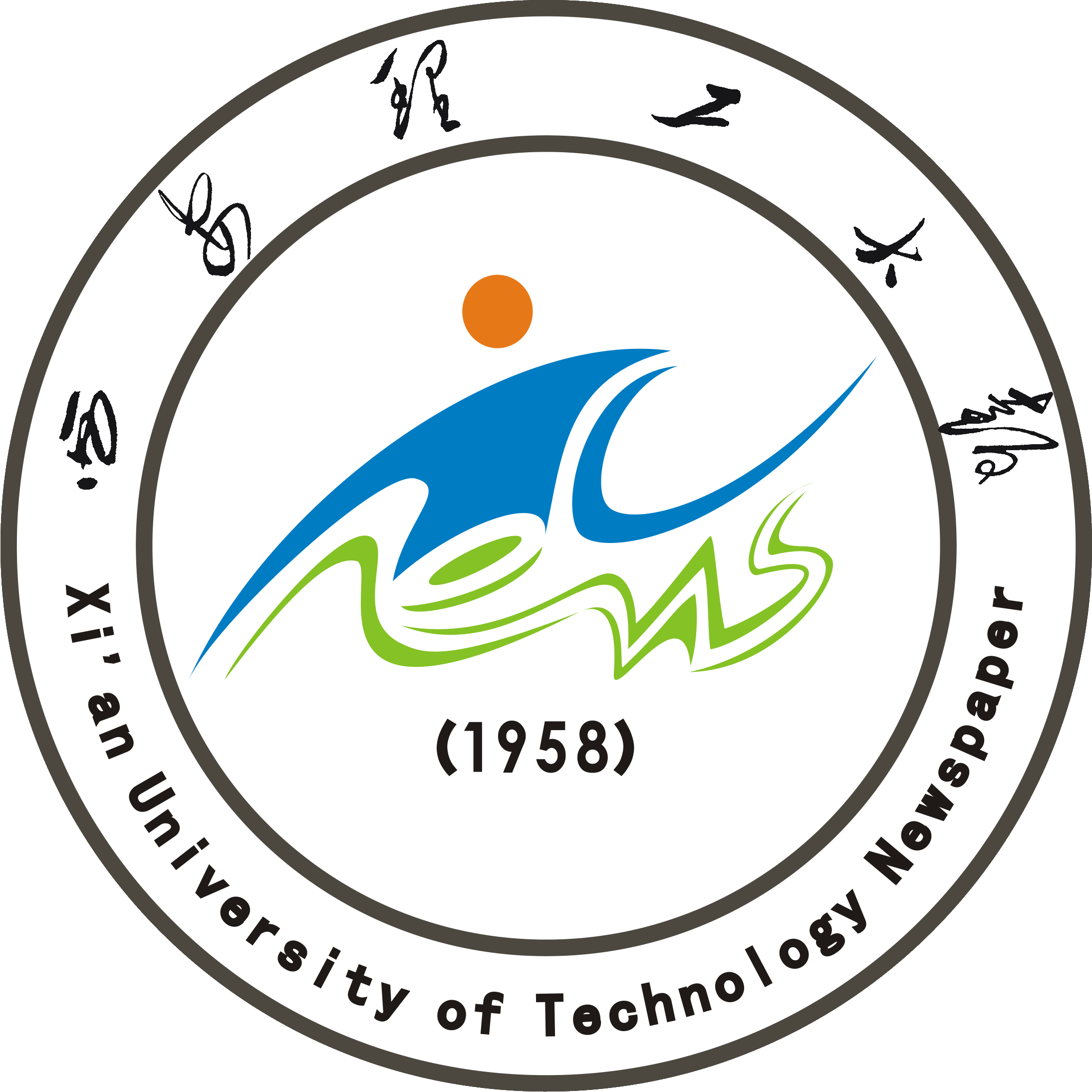空气好像是热到了沸点,不降温。
候车亭里坐了很多人,可是毕竟每个人等待的车都是不同时间的,所以,仔细看还是仍旧可以找到位置。我和我爸坐下来,与其他人一样,做着同一件事——等待。
或许不同的只是每个人的思索,而对于我,思索定格在眼前的这位老太太。说是眼前似乎有点不写实了,隔着一层脏兮兮的玻璃,我只能勉强看清她的表情,这也好,隐去了脸上的些许老年斑。她有一双红红的手,好像是年轻时劳累的缘故,关节肿了出来,很像我的姥姥,这一代人,可能都是这样吧。
我喝了一口水,冰凉滑进喉咙,
“拿瓶水”
“要不要冰”
“冰的冰的”
是个外地的小伙儿,很结实,实际年龄可能就比我大上两三岁吧,或许比我小,我总是觉得外地的孩子在身形上总是比城市孩子显得大,可是脸上总带着那么两朵红,是怎么也丢不掉的淳朴,我希望这花儿别败,就那么开着。
老太太整了整自己的卫生帽,额角渗出了汗,在玻璃后面显得特别清澈。老人似乎特别少出汗,皱皱的皮肤,像是极其缺乏地下水的土地,不免显得有些疲惫。不都说人老了就是该享福的时候了吗?不过,这老太倒是津津有味的开着小铺。是因为有个不孝顺的子女或是有个尖酸刻薄的儿媳,还是过不惯清闲的生活。想看看清楚她的脸和眼,又被人群给挡了住,热闹的人群中,我们可能又丢失了一双充满欢乐的眼睛还是一双无奈于生活的呢?
火车站的提示板上红色的字在滚动着,一班又一班的火车从一个地方开往另一个地方,送着不同的人,停靠在哪一站,也许是过客,也许就从此生根。老太太和她的杂货店,在候车室里,跟着钟表的转动,由春到冬,幸好窗外都是钢筋水泥,还多少模糊了一下时间的疾步。
身边的人们纷纷起身,拿起自己的大包小包,走向进站口,我突然想到,好像也到时间要进站了,
“爸,到点了?”
“走,走”
走,走,每个人都在走,走去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才能到自己真正想到的地方,而我们又想去什么地方,挺远的,也挺难的,我只能这样形容。一个一个的脑袋簇拥着向前走,而你知道,有时候过河的人很多桥却只有一座,谁好像都看不清了,好像都是一样的人,为了那个不知到是对错的终点雕琢自己。
看不清了,人群向前,找不到自己的样子,握着迷茫地坚定,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