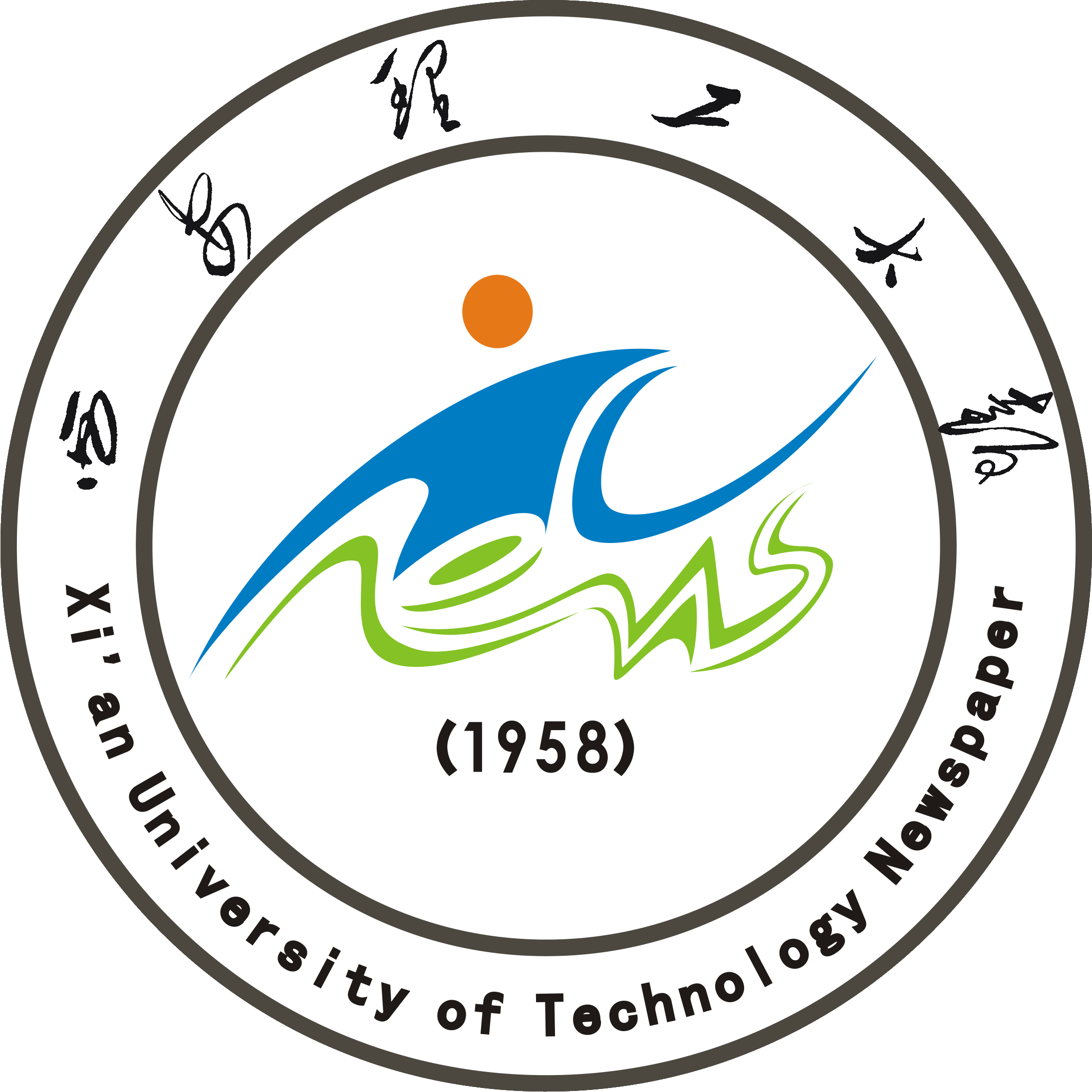我公开地把心灵献给严酷痛苦的大地,往往在神圣的夜晚许诺要忠贞地爱它,至死不渝,承受其命定的沉重负担,一无所惧,决不蔑视它的任何一个谜。这样一种致死的纽带把我和它联结在一起。
——荷尔德林
社会中有了太多奴隶人。存在着情欲的罪恶与逻辑的罪恶。我们处于预谋与完美的罪恶的时代。我们的罪犯不再是那些身无寸铁的孩童,他们以爱为理由替自己辩解。相反,他们是成年人,其托词是无可辩驳的:哲学可以为一切效劳,甚至可以使杀人犯变成法官。
在《呼啸山庄》中,希思克利弗为了占有卡蒂而屠杀整个大地,但他并未想到说这种屠杀是合理的或者拿制度为其辩护。他完成了这次屠杀,其全部信仰就在此终结。他这样做可能是出于爱的力量,还有性格。爱的力量是罕见的,这种杀人是异常的,于是带有破坏的色彩。然而,自从人们信仰一种学说,自从罪恶受理性控制,它便如同理智本身一样繁衍增多,有了三段论一样无可争辩的性质。它如同呼喊一样是孤独的,同科学一样是普遍的。它昨天受到审讯,今天却制定法律。因此,我们需要反抗。
何谓反抗者?一个说“不”的人。然而,他虽然拒绝,却并不放弃:他也是从一开始行动就说“是”的人。一个奴隶,一生都在接受命令,往往觉得新的命令是无法接受的。这个“不”的含义是什么呢?
它可以意味着“这类事情持续得太久了”,“到此为止还可以,再超过就不行了”,“你走得太远了”,也许还意味着“有个界限是不可逾越的”。总之,这个“不”肯定了一条界限的存在。从反抗者的某种感情中也可以发现这一界限的想法,这种感情就是他要将其权利扩展于这个界限之外,但越过此界限即有另外一种权利约束他。因而,反抗行动同时也就是对视之为不可容忍的侵犯予以斩钉截铁的拒绝,朦胧地相信他有一种正当的权利。更确切地说,反抗者这时怀有他享有“……权利”的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反抗者若未怀有自己是理直气壮的这种感情,便不会有反抗。正由于此,反抗的奴隶同时既说“不”又说“是”。他在肯定上述界限的同时,也肯定他所怀疑的一切,并想使之保持在这个界限之内。他固执地表示自己身上有某种东西“值得……”,要求人们予以关注。他以某种方式表明自己受到的压迫不能超过他认可的程度,以这种权利来对抗压迫他的命令。
人厌恶对自己的侵犯。同时,在一切反抗中,他都完全坚持自己身上的某种意愿,因而必然坚信一种价值判断,在危难时仍坚定不移。直到此时,他保持缄默,陷入绝望之中,虽对不公正的境况仍加以接受。缄默,会令人认为他不进行判断,一无所有,而且在某种情况下他的确一无所求。绝望同荒诞一样,一般说来,对一切皆进行判断,并渴求之。而在具体情况下,却毫无判断,一无所求。沉默便清楚地表明这一点。然而,他一旦开口讲话,即使是说“不”,便表明他在判断与渴求。反抗者,从该词词源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在主人的鞭笞下昂然行进,进行反抗,以自己所赞成的一切对抗自己不赞同的一切。并非一切价值观念都会引起反抗,但是一切反抗行动都不言而喻地以一种价值观念为依据。是否至少会涉及一种价值观呢?
从反抗行动中产生了意识的觉醒,不论它是何其朦胧。他突然意识到人身上有某种东西应该是属于自己的,哪怕这种情况为时短暂。这种自主性直到此时尚未为他所真正感觉到。在进行反抗之前,奴隶忍受了一切压榨。他那时甚至对主人的命令往往俯首帖耳,完全驯从,尽管这些命令比如今招致他拒绝的命令更应激起反抗。他对之逆来顺受,也许内心并不愿接受,但他更关心的是眼前的利益,而尚未意识到他的权利,于是保持缄默。当他失去耐心而变得焦躁时,便开始对以往所接受的一切采取行动。这种冲动其实以往经常出现。奴隶在拒绝主人令人屈辱的命令时,同时便否定了他自己的奴隶地位。反抗行动使他比单纯的拒绝走得更远,甚至超出了为其对手确定的界限,如今要求以平等的身份对待自己。这种难以遏制的最初的抗争逐渐使人与抗争融为一体,使其一言一行均表现出抗争。他想让人们尊重他身上的这个部分,并将其置于其余一切之上,钟爱它胜过一切,甚至生命。这个部分对他说来成为至高无上的财富。奴隶以前处于委曲求全的境地,现在一下子要求获得“一切”,否则便“什么也不是”。他的觉悟随着反抗而苏醒。
人们看到,这种觉悟既想得到尚且相当模糊的一切,又想到了“什么也不是”,这表示有可能为此“一切”而牺牲自己。反抗者想成为一切,完全拥有他突然意识到的这笔财富,希望人们承认他身上的这笔财富并向它致敬,否则他便一无所有,也就是说,最终被支配他的力量剥夺一切。他如果被夺去他称之为自由的神圣事物,便会接受死亡这最终的结局。宁肯站着死去,而不跪着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