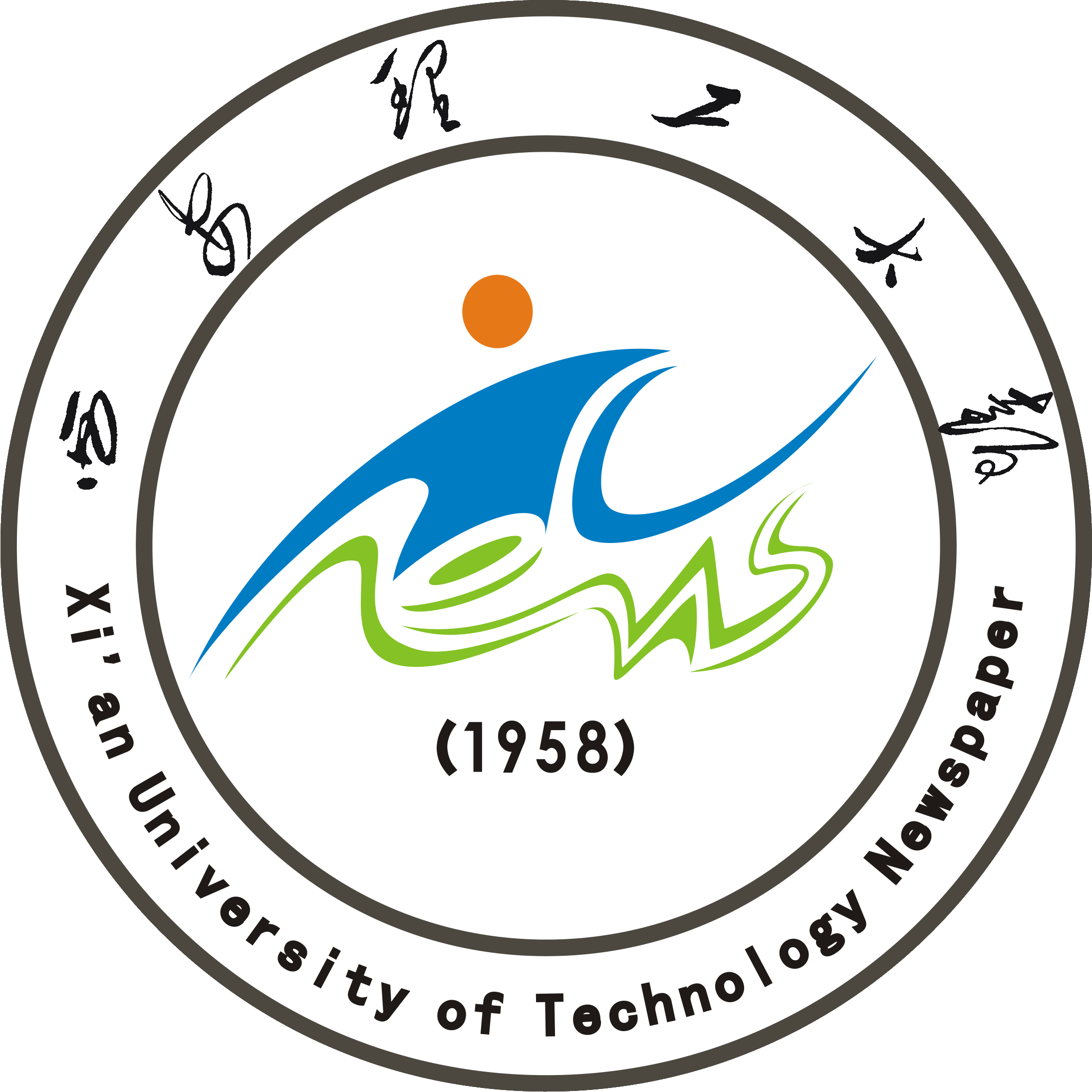“都收拾好了,明早我们就动身。”小张冲老板阿宽挥挥手,抽出把椅子坐了下来,大口喘着粗气,总算是把店内的杂物都清理干净了。阿宽站在店门口,背着手向外张望,往日生意红火的美食街此刻像被按下了静音键,偶有行人路过,也不是冲着照顾阿宽的生意而来,神色匆匆,步履不停。阿宽叹口气,抬头望望店门外悬着的灯幅——“正在营业中”,伸手触及开关,闪烁着的彩色字体归于黑暗,只留店内的照明灯作为整条街最后的光亮,倔强地长明着。
小张让阿宽和他回自己的出租屋去凑合一晚,阿宽笑称自己熟悉了店内的油盐酱醋味,换个地方,会睡不着,今晚就让他再陪陪自己的小店,当作最后的告别。店里的暖气已停了段时间,没有人来用餐,也不用再遵守着“顾客至上”的原则,阿宽觉得开着也是浪费。虽已到三月,但仍有几分凉意,阿宽蜷缩在桌角,摸摸口袋想点根烟来暖和一下,却摸出了一把零钱。
A 城从去年开始已经全面实行网络支付,叼着钱币的金蟾趴在人工收银的柜台前目光灼灼,但早已无人问津。而阿宽却有次一大早揣着把零钱放进了柜台抽屉里,冲着小胡信誓旦旦地讲,一定会用的到,小胡皱着眉表示不能理解。小张瞥见阿宽出了店门,拽拽小胡衣角,贴着耳朵说话。
昨晚小张值班,趴在柜台撑着脑袋数时间,恍惚间好像看见圣诞老人背着大口袋来店里作跨国交流,揉揉眼睛定了神,原来是一位慈眉白发老奶奶领着一只粉妆玉砌的小娃娃进了店。两人都穿着红衣服,小娃娃穿红羽绒裙,老奶奶穿大红袄,不过小娃娃更“红火”一些,因为她还系着两个夸张的绒绒球,垂下的红丝带随着辫子一起欢跳。小娃娃饱餐了一顿,一双大眼睛困成了眯眯眼,东倒西歪靠着老奶奶,两个红脸蛋又好像随时要打醉拳。老奶奶抱着小娃娃呵呵笑,挪到柜台结账。小张把二维码的牌子向前一立,同时老奶奶从口袋摸出纸帕拆着,捏着一张纸币递了过来。小张还没缓过神,一只手抢在他前面把纸币又按回了纸帕里。阿宽冲老奶奶摆摆手,
“店里的零钱包我忘在家了,您下次抽个空过来付吧,没空就算了,哈哈……哈哈。”老奶奶拖着小娃娃出了店,好像两个火球重新融入了雪夜里。
小张以为老板只是一时兴起,没想到第二天阿宽真的揣着把零钱交给了小胡。隔壁是家小卖部,常有在附近工地打工的人来买十二元一盒的烟来抽,工地的人带手机不方便,大多都是卷着一叠浸着汗渍的零钞过来买烟,这家小卖部也就成了 A 城里为数不多还保留着纸币交易的店铺。阿宽便是从隔壁店主那里换的零钱吧,小张看着那叠零钱,似有钢筋水泥的气息弥漫开来。
第二天,老奶奶又带着她的小孙女在晚上七点准时出现,收银的小胡告诉她已经可以用现金支付,老奶奶笑眯了眼睛,看过去脸上又添几道皱纹,说要将两天的饭钱一起付清。她将手绢从口袋里摸出铺在收银台上,一只手费力地解着,另一只胳膊上还攀着小孙女。小家伙吃饱喝足,倚着奶奶已经昏昏欲睡。老奶奶望着臂弯的小孙女慈爱地笑,阿宽靠着柜台歪着脑袋望着老奶奶憨憨地笑,小胡望着阿宽一脸疑惑,小张继续扯扯小胡衣袖,表示自己知道为何会这样。
去年年底聚餐,两张桌子并在一起,大伙围在一起吃火锅。热气沿着锅沿往上冒,小张看不清桌对面阿宽的神情,只见他一手撑着桌子,一只手举着啤酒瓶儿,缓缓站起来,说要唱一首歌给大家助兴。歌曲调子很熟悉,是《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小张也会跟着哼哼几句。不过阿宽唱的不是“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而是“我们坐在高高的玉米堆上面”,小张便知道阿宽又想起他外婆了。
阿宽家有一大片玉米地,每次丰收,玉米便像座小山一样堆在院子里,阿宽便颤颤巍巍地登上玉米山顶,幻想自己是这座村庄的首领,站在最高处登高望远,一统村落。外婆坐着把小藤椅,剥着玉米外衣,挑几个颗粒最饱满的单独放着,阿宽便知道最近的早中晚饭都要被玉米家族承包了。炒玉米、煮玉米,玉米羹、玉米饼,一个灶台,一把铁铲,外婆无所不能。不过阿宽渐渐长大,知道了玉米秸秆没有甘蔗啃着甜,知道了天底下还有比玉米做法更多的食物,阿宽决定出去闯一闯。坐在客车上,看着窗外的风景匆匆掠过,远离了一片片金灿灿的玉米地,远离了不超过一百口人,每家每户的八卦新闻都能打听得清清楚楚的小村落,也远离了什么也不会,只有针线活和剥玉米技术格外好的外婆。
阿宽是看到小孙女的奶奶,想到了自己的外婆。小张信誓旦旦,对小胡悄声说。小胡点点头,决定以后细细观察一下这位奶奶和小张描述的阿宽外婆有何相似之处。可是老奶奶再没有来过,她的那位走起路来像团小火球的小孙女也没有再出现过。过了两月有余,小胡终于再次看到了“小火球”,头发长长了一些,头顶的辫子不再向上翘,而是低低地垂下来,两个红色绒绒球也换成了两根简单的黑色皮筋。不同之前晚七点的准时光顾,此时正是中午时分。小胡左顾右盼,都未看到老奶奶的身影,这才注意到小女孩旁边站着位年轻女郎。女郎掏出手机看看时间,冲着小女孩皱眉,催促她吃快一些。小女孩低着头,舀着饭急急忙忙往嘴里送。女郎盯着手机时间,踩着细跟的鞋时而跺两下,小女孩手中的勺子便碰着碗壁丁零当啷。不等小女孩吃完,女郎便推开碗碟,将女孩从椅子上拽下来,一手挽着书包,一手拎着女孩,匆匆出门去。
“真不该让你奶奶过来照顾你,现在吃饭也这么拖延,还好她现在回乡下了,让她再管下去你还要成什么样子。以后还是吃快餐吧,这种店等起来真浪费时间。”女郎说话像是倒豆子,语速极快,配合着她三步并两步的步伐,还未走出店门,已说了一长段。
望着眼前的这叠纸币,没沾过几滴墨水的阿宽竟也能文绉绉地喃喃一句“物是人非”。店内的杂物已经清理完毕,只剩几件阿宽还没能决定它们去处的物件在柜台前堆着。阿宽睡眼朦胧,眯着眼一件一件打量,手指触着物件,往事一一浮现。
左手边缺了口的陶瓷碗盖,是附近工地的一位小哥碰到地上的。工地会管饭,大家集中吃完,好节省时间去午睡,休息好了,下午接着赶工。小哥有日和同工地的另一位工人闹了矛盾,谁也看不惯谁,干脆中午出来吃饭,眼不见心不烦。
“老板,这有辣椒么?”小哥扯着嗓子冲阿宽喊,阿宽从后厨取出一个陶瓷罐,放在桌子上,提醒他只能放一点,他家乡的辣椒酱以巨辣而出名。谁说他阿宽是形单影只离开家乡?他阿宽要带着家乡品牌去扬名立万。
不听阿宽言,吃亏在眼前吧……阿宽看着大哥舀了满满一大勺辣椒酱加入饭里,扯了扯嘴角。果然,下一秒大哥便涨红了脸,辣得直冒汗,把碗碟推向一旁,慌忙间放在桌边的陶瓷碗盖便拂到了地上。
“哐当——”大哥望着地上的碗盖慌了神,随即站起身摸口袋,说要赔钱。阿宽冲大哥摆摆手,俯身捡起碗盖,“只缺了个口,还能用。”大哥抓抓脑袋,加了过多辣椒酱的饭也不能食用了,结了账就匆匆离去。还得赶时间去睡个午觉,下午上工可马虎不得。阿宽冲小胡要了张纸,写了“此辣酱巨辣,放前请斟酌”的字条贴在陶瓷碗上,拎到桌角放着。
此后每天,陶瓷碗便毕恭毕敬地站在桌角等待工地小哥大驾光临,不过小哥再也没来过。阿宽甩锅给陶瓷碗,“都是你太辣了,才把小哥吓走了。”其实阿宽心里清楚,工地打工挣的都是血汗钱,每一笔都要小心翼翼整理好寄回家里的,没有人会放着免费的工地餐不吃,出来点两个小菜自己快活。一时气结出来吃一顿,回到平板搭建的临时宿舍里,怕是又要暗自恼悔。
右手边是一副字画,发黄的纸张昭示着已有些时日,但毫不见压痕,是小张下午才从裱框里取出来的。经常来店里吃饭的熟人有时会打趣阿宽,饭店里却要挂一副字画,是要改换门面作书画店吗?阿宽从来都是笑笑,不回答。
阿宽初来 A 城,便用手头不多的钱去报了厨艺培训班,看到电视里的广告将厨师行业的发展前景讲得绘声绘色,阿宽觉得这会是个好出路。趴在案板前用刻刀雕萝卜花时,脑海里也幻想着他穿着厨师服站在五星级酒店里拿着锅铲对着食材“挥斥方遒”,嘴角咧得幅度过大,
“哧——”一片萝卜花瓣刻歪了。直到从培训班毕业,拿着本培训班老师自吹自擂说是含金量很高的毕业证书去寻求酒店老板慧眼识珠时,才发现是自己过于天真。阿宽在树荫下踱着步,摸摸塌下去的肚子,思忖着不然就去刚才的那个小饭馆当个帮厨吧,谈什么理想,先谈谈今天的晚饭吧。
“岁月不待人,不待人哪。”阿宽正准备迈步,忽听有道苍老的声音自耳边划过,原来是身旁摆字画摊的老者。老者一边自顾自说着,一边收拾着字画,准备收摊。老者动作很快,不一会儿多幅字画便整理完毕,一卷一卷放入布袋里,准备回家。
“哎,年轻人,剩下的那幅字画就送你吧,太重了,老头我背不动咯。”原来其他字画都已装好,只留一幅形单影只在地面上躺着。不等阿宽回答,便背着布袋扬长而去,喃喃自语又是一天光阴匆匆而过,自己的字画摊却依旧无人问津。身旁一直看热闹的清洁工把字画捡起来,小心翼翼地卷好,递给阿宽,望着老者的背影无奈摇头。听一直打扫这片区域的清洁工讲,老者本喜爱书画,但为了柴米油盐,在其他的岗位上一待便是四十多载光阴,终于熬到退休,可以重拾起字画来,却已经手生,年少时被夸奖的颇有天赋,到现在也成了人们饭后唏嘘的江郎才尽。阿宽展开字画来瞧,虽不懂画的是什么,但觉得配色很有意境。“是那些人不懂欣赏罢了!”卷了字画,阿宽背朝着准备谋碗饭的餐馆扬长而去。
“光阴难再复,难再复……”老者的面貌很快便在阿宽脑海里模糊,但这句话却一直在耳畔不断地循环播放。
阿宽回到出租屋,同合租的在此地打工的小张借了张纸,给那座任由他 逃 出 来 的 小 村 庄 写 了 第 一 封 信 。“喂,我打算从亲戚那里借笔钱开家自己的饭店,来入伙吗?”阿宽折起写好的信件,向同租舍友发出邀请。正丢了工作准备明天去人才市场碰碰运气的小张闻言转身,欣喜点点头。小张人如其名,张罗起门面选址、店铺装修、食材购进可是一把好手,阿宽的餐馆很快便等来开业的一天。小张对自己的审美水平很满意,客人们也对店内的装修风格赞不绝口。只有一点不好,便是墙上挂着的一幅字画,和整个店的装修风格不搭,就如一幅西方油彩画中突然画了了几朵墨梅,分开都是绝佳,合在一起便意境全无。阿宽不理会,自顾自地把字画小心翼翼挂上去,就挂在店里最显眼的位置。若哪天那位老者碰巧来店里吃饭,一抬头便能看见。
翻着旧物,伴着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不知觉间已是天明。小张专挑着积雨的水坑踩,一路蹦跳到店门,“走吧,去赶八点半的动车!”望向店内却傻了眼,“你这是做什么?”阿宽把昨天整理打包好的物件又一件件摆放了回去,各自归位,一件不少。
“我不打算把店卖出去了,我就呆在 A 城哪也不去,我等一切都好起来。”见小张像惊掉了下巴,阿宽故作轻松,帮他抖抖衣肩上的落雨,“这叫什么,‘空山新雨后’,是不是?”附近学校的中学生总喜欢来店里一边吃饭一边还要在桌上撑着语文书,抽空念几句诗词背记一下,不知道那位中学生后来语文默写得了几分,他阿宽倒是跟着听了几遍,记得八九不离十了。
“那我也不走了。”小张把行李箱推了进来,靠在墙边。从小看了郭靖大侠死守襄阳城的片段便视郭靖为人生楷模的小张,觉得自己此时颇有几分英雄气概。
“那你我兄弟二人就镇守此地,等一众病毒退散之时,我们便候在这里,等待第一位客人的光临。”阿宽学着小张喜欢的武侠剧里的人物,沉着嗓子讲话。小张闻声打个激灵,冲阿宽作暂停手势“喂,学得一点都不像!”
疫情蔓延得突然,阿宽特地拜托一位老先生写的烫金对联也来不及贴,就匆匆收了起来,为了悬挂灯笼而新挂的粘钩,也孤零零地垂着。写着店铺名称的牌匾是由于超了预算,临开业前才急匆匆找了家新开业的店打了折扣订做的,此时已脱了漆,也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小店面日后生意会这么红火,再顶着这块小家子气的牌匾,着实有些突兀。小张站在外面慢慢倒退,从局部再到整体,思忖着等能重新开业之时,要添些什么装饰,手抵着下巴打量着门店,冲着店里的阿宽喊话,“喂,我们的牌匾是不是需要更换一下啦?”
店内的阿宽正划着手机页面,最新消息已经播报,情况正在好转,这场阴霾就快要消散。太阳赏个脸,将雨后初晴的第一缕阳光赠予这个小店。阿宽伸伸懒腰,走出店门,与满脸灰尘抱着拆卸下来的旧牌匾进店的小张撞个满怀,
“老板你说,咱们要不索性再换个店名,新气象嘛!”小张拽着阿宽衣袖,一个劲地把衣服上的灰往阿宽身上蹭。
“就叫……故人归。”阿宽顿住脚步,缓缓道出。
最漫长的凌冬时节终于要离去,道路旁蕴着的含苞待放,只待掌管四月天的花神一声令下,便准备一场满城花开。到时会有过客打马路过,会有旧友闲来问盏。但不论初次相遇,亦或是久别重逢,踏入门槛的一刻,便是故人归。